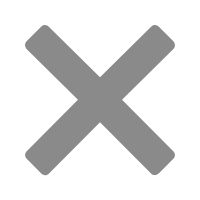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二九九章 誰才是獵人2_2
野豬似乎還沒完全斷氣,在我身上喘息,掙紮著。我說不出是該為殺死野豬高興,還是該為逃過一劫而喜悅。
就在我感覺快無法呼吸,身體也快被壓扁時,桃二叔終於趕過來,連拖帶拽才將野豬從我身上拉開。估計是因為臉上的血,他不停拍著我的臉問怎麼樣,傷著哪兒瞭,有沒有事。
我有些想笑,可胸口很疼,又笑不出來。直到我說清沒事,是野豬的血後,他才放松下來。我慢慢爬起來,桃二叔拿起隨身那個裝水的皮袋,到野豬脖子下接血,叨念:「到大城市把你的膽兒都磨光瞭,從小就在山裡跑,看見獵物怎麼能腿軟,還及不上小時候。還記得以前跟著我,到山裡抓蛇賣的日子不?」
「當然記著,我高中,大學時的生括費,全靠它來的。」我點頭道,想到那些在山裡轉悠的日子,有些懷念,感覺已經離我很遙遠。
「來,把它喝瞭。」桃二叔把皮袋遞給我。
「幹嘛?」我有些疑惑。
「野豬血,喝瞭能暖身,旺血氣。」桃二叔說。
現在還能聞到臉上的血腥味,我有些猶豫。
「怎麼?這點膽兒都沒瞭?當年吞蛇膽的時候,可是眼都不帶眨的。」桃二叔笑道。
我咬牙接過來,試著嘗瞭一小口。剛流出的血,溫溫的有點熱乎,還有點咸澀。
「大口點,又不是小娘們兒。」桃二叔慫恿道。
剛才被嚇的腿軟,已經夠丟臉,現在被說成女人。我狠心張口,像喝酒般,咕隆咕隆,喝下幾大口。
「哈哈,這樣才對嘛!」桃二叔笑贊道。
雖然不是酒,但喝到體內,很快全身就熱乎起來,像是喝瞭口滾燙的水進聞裡。雖然那陣腥味的難聞,還是勉強能忍受。感覺很暢快,像是突然醒悟般,仰頭又咕隆咕隆灌瞭幾口,鮮血順著嘴角,滴落到身上,我也不管。
確實如桃二叔所說,我不是嬌生慣養的金枝玉葉,而從小就是個在泥坑裡打滾的癩蛤蟆,在大山裡摸爬的獵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獵物。獵人就要比獵物更具野性,外面的花花世界確實美麗,迷人,讓人沉醉,但我原本就不屬於哪裡。這些年的迷失,磨光瞭我的野性,讓我隻會躲閃,逃避,妥協,把我變成瞭一條聽話的寵物狗,供人觀賞,玩弄,嘲笑。
大山裡出來獵人,應該是那個捕捉,玩弄獵物的人才對。我不能在這樣被人玩弄,嘲笑後,還要忍受屈辱,舔著臉,搖尾乞食。即使當狗,也要做條機敏,勇敢,兇猛的獵狗,瞄準獵物,就要勇往直前,咬住獵物,就絕不松口。
「你怎麼樣?沒事吧!」桃二叔看我半天不說話,擔心道。
我搖頭表示沒事,又猛喝瞭口皮袋裡的血,遞回給桃二叔。他也不客氣,笑瞭笑,接過去就猛灌瞭幾口。他仰起手腕時,我才看到他手臂上,哪條五,六公分長的驤人傷口,擔心道「手上的傷怎麼樣?」
「沒什麼大事,就是點皮外傷,死不瞭。」桃二叔看瞭眼傷口,滿不在乎的說。
話是這麼說,我還是有些擔心,山裡沒有調配好的藥物,但土產卻不少。不知是因為喝瞭血,還是被嚇瞭跳,腿腳也利索多瞭。很快在不遠處找到幾株艾蒿,撇瞭株回來。
常年在大山跑,自然明白,桃二叔也不矯情,接過去揉爛,貼在瞭傷口上。
看著地上已經斷氣的野豬,感覺很幸運,還有點僥幸,如果沒有那麼多如果,或許我今天真危險瞭。估計它起初沖出來是想引開我們,保護自己的幼仔,是大黃把小野豬趕出來,才把它又引瞭回來。
幸好最後被狗拖住,減慢瞭野豬的速度,不然幾百斤的重量,加上狂奔而來的速度,即使能殺掉它,也會被幾百斤撞斷幾根肋骨。經過這陣折騰,人累瞭,幾條狗也累瞭。休息瞭一陣,桃二叔就地砍瞭根彈力很好的木棍,把豬綁好抬著下山。我自然沒耶大力氣,大部分重量靠二叔撐著,綁的時候,他就把野豬放的靠近後面。
路上歇瞭好幾次才到傢,真是太久瞭,感覺腰都快斷瞭。聽到我們捕到野豬,村裡的人都跑來看,聽說是我刺中要害後,都不停的誇有能耐,弄的我還很不好意思,差點就死在山上,下不來瞭。
母親看到我滿腔的血,還很擔心,解釋瞭幾遍是野豬的血後,她才放心。當天晚上就把野豬剝瞭皮,桃二叔硬給我們傢塞瞭半截,起初我還不好意思要,畢竟他是為保護我受的傷,而且還救瞭我的命。但他執意讓我搬回去,想到在傢的父母,後來也沒在推辭。
在場的村民也一人分到兩斤,村裡的規矩,捕到大貨要慶祝。所有老少爺們當晚聚在一起,出酒的出酒,出菜的出菜,燒起篝火,就在村前的大壩裡,一起吃瞭頓酒。
雖然喝的是燒酒,吃的也不是什麼山珍梅味,但所有人都喝的很痛快,吃的很高興。大碗裝酒,肉也切的很大塊,卻沒什麼感覺不妥,看著那一張張質樸的笑臉,反而覺得親近,自然,熟悉。
看著他們,彷佛自己又回到從前,從新融^到這個地方,那晚真喝醉瞭,但感覺到很久沒有過的痛快。接下來幾天,就在傢陪母親說說話,偶爾幫父親打打下手。桃二叔手傷瞭,雖然不是很重,卻沒法幹括,沒事就到他傢去轉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