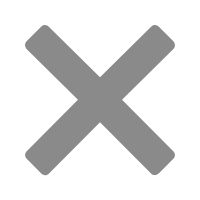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05章-短暫的蜜戲
“媽媽,媽媽”李湘哭哭咧咧地站在地板上,我張開雙臂,緊緊地抱住她,欲將其擁到床鋪上。
李湘難堪地扭動著嬌巧的身體,我的手無意間摸到她的小圓屁股上,頓時感覺到一片潮濕。
我低下頭去一看,乖乖,李湘的裙子早已被尿液浸得濕漉漉,騷濁的尿液順著細腿緩緩地漫流著,直至流進雪白的絲襪裡,看到我茫然的神情,李湘羞愧難當地低下頭去,我急忙拉開大紅櫃,拽出姐姐的內褲和一條舊褲子:“來,換上姐姐的褲子吧!”
“嗯,”
李湘柔順地點點頭,主動褪下自己的濕內褲,露出瞭潔白光嫩的小屁股,我乘機抓摸一把,手上立刻一片濕乎乎,我將手掌放到鼻孔下嗅聞一番,李湘嬌澀地笑瞭笑,秀麗的臉蛋上掛滿瞭晶瑩的淚花。
我撐開姐姐的內褲,李湘溫柔地伸過兩條細嫩的大腿,我將內褲套在她的腳脖上,我一邊往上套著內褲,一邊故意將李湘的雙腿屈曲起來,胯間的小便非常可笑地分張開,露出如豆的小肉頭和淡粉色的小肉眼。
我貪婪地用手指插捅瞭幾下,李湘本能地抖動起身體,她抬起頭來,呆呆地望著自己的身下以及我那頻繁進出的小手指。
“哈,”
當我將姐姐的舊褲子套到李湘的腿上時,褲腿竟然長出大半截,將李湘的小腳掌全部埋沒住,我隻好幫助她將褲腿一圈一圈地往上卷套著:“哈,你的個子太矮嘍,姐姐的褲子長出一大截啊!”
卡斯特羅這傢鄰居的男主人,姓周,名廣義,此人身材高大、相貌灑脫、英俊,畢業於一所名牌大學,滿腹裝著高深的專業知識。
並且,非常驕傲地研究出一套據說是最為先進的采金船技術,興致勃勃地四處推廣,卻永遠也沒有逢遇到識貨的伯樂,真乃生不逢時啊。
時至今日,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仍然毫不氣餒地拎著裝滿采金船技術資料的公文包終日東奔西走,毫無目標地尋找著永遠也不會出現的投資者。
然而,在道德修養方面,我們這位學富五車的周工程師卻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也許是大學裡沒有道德修養這一相關專業的緣故吧,我們的周工程師脾氣暴燥,蠻橫無理,其所作所為與他“廣佈仁義”的名字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因此,單位裡的同志們送給他一個無比響亮的外號——周大驢。
外貌既英俊又瀟灑的周工程師,卻經常為一些毫無意義的、雞毛蒜皮般的瑣事與鄰居或者同事們爭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搞得四鄰不安,雞飛狗跳,孩子哭、大人叫。
然而,我們的周大工程師則是樂此不疲,與人鬥是周大工程師的最愛。
如果實在沒有對手與之相鬥時,煩悶之餘的周大驢便與自己的老婆鬥。
“操你媽!”
“……”
寂靜的深夜裡,隔三差五便會從幽暗如冥界的小走廊裡傳來周大驢夫婦兩人兇狠的、但卻是極其單調的對罵聲,把我從甜美的夢鄉中驚醒。
可是罵來罵去,直至罵到紅彤彤的太陽已經出來值班,周大驢夫婦兩人所使用過的詞匯永遠都是:“操你媽”這三個字。
“唉,他們還會不會罵點別的什麼呢!”
被吵醒的爸爸翻轉一下身體,沒好氣地嘟囔道。
沒有,從來沒有,周大驢夫婦倆人不知疲倦地對罵瞭數十載,直至從豐華正茂罵到白發蒼蒼,最後,終於將老婆罵進瞭骨灰盒,然而,他們所使用的詞匯,除瞭“操你媽!”
這個三字而外,從來沒有使用過任何新的詞匯,也許這三個字是國粹的原緣吧!
“操你媽!”
“……”
周大驢的小兒子與我年齡相仿,有其父便有其子,周大驢的這個小兒子,在宿舍樓裡以刁頑、陰損而路人皆知,人送外號周扒皮。
偶爾,我也會溜到周大驢傢裡與他的小兒子周扒皮遊戲玩耍。
那是一個死亡般沉悶的傢庭,那是一個讓人窒息的傢庭。
在昏暗的、潮濕的,充溢著令人返胃的異臭氣味地房間裡,周大驢叼著嗆人的大煙袋,戴著污濁的近視鏡,煞有介事地翻閱著一本又一本即厚且重的書籍,而對面的墻壁則用木板釘成天然的大書架,從地板直至高聳的天棚,毫無規則地擺放著成山的書籍,許多書籍周大驢大概永遠也沒有翻動過,如磚的書籍上積著厚重的灰塵,散發著剌鼻的酸腐味。
“哼哼,”
一生也沒有尋覓到知音,永遠也沒有將自己漚心研究出來的采金船技術成功地推廣出去的周大驢,看見我坐到他的椅子旁,他悠然地轉過寬闊的脊背,拉著老驢臉,將沉甸甸的檔案袋推到我的面前:“小傢夥,你知道嗎,這是我研究出來的新技術,……”
“嗯,”
我怯生生地點點頭:“是的,我聽爸爸說起過你,……”
“啊——”
聽到我的話,周大驢的驢臉頓然一亮,閃過一絲得意的光芒,他興奮得像個孩子似地打開瞭檔案袋,掏出一疊又一疊的圖紙,以及天書般的文字材料,如數傢珍,喋喋不休地沖我講述起來,直聽得我如入五裡霧中。
“哎呀呀,”
周扒皮的媽媽,周大驢的黃臉老婆沖著興奮得渾身直打冷戰的周大驢沒好氣地嘀咕道:“哎呀呀,哎呀呀,我看你是不是有病啊,病得還不輕吶,無論見到誰,都要沒完沒瞭地講你的采金船,這不,跟這個還沒有豆腐高的小屄小子你也要嘮叨嘮叨,就像他能聽懂似的,你煩不煩啊,……”
“我樂意,”
周大驢像驢一般地沖著黃臉婆吼叫起來:“我樂意,用不著你管!操你媽!”
“哼,”
黃臉婆自討沒趣,滿腹的怨氣無處可泄,一轉臉,看到身旁的周扒皮,立刻沖著無辜的兒子發泄起來:“快點吃!”
周扒皮的黃臉媽媽不耐煩地催促著,周扒皮端著一碗冷冰冰的面條,在黃臉媽媽惡毒的謾罵聲中,狼吞虎咽地往嘴裡撥塞著。
我偷偷地瞅瞭瞅周大驢的黃臉老婆,我的老天爺啊,我的媽媽喲,不瞅則已,這一瞅,我嚇點沒吐出來。
周大驢的黃臉老婆那臃腫的身軀活象一頭叫春的老母豬,那一臉厚厚的贅肉顯露著無比邪惡的神情,圓鼓鼓的小眼睛閃著陰森森的、仇視一切的目光,當她挪動著笨拙的身體時,立刻傳過來一股股令人嘔吐的騷臭氣味。
我至今也無法想象我們可憐的周大驢是如何與他母夜叉般的黃臉老婆共同生活的,更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居然生出瞭那多的孩子。
母夜叉的婆婆,亦就是周大驢的母親因不堪忍受兒媳婦的虐待而跳樓自殺,鑒於此,母夜叉不得不在監獄裡反省瞭數載,盡管她很不喜歡那個地方。
亦因為這個緣故,宿舍樓裡的人們都叫她“大罪犯”有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得罪瞭周扒皮,兩個人在走廊裡撕打起來,母夜叉聞訊趕來,一把將我推翻在地,她惡狠狠地沖著我吼叫道:“雜種操的,看你再敢打給我的兒子,老娘剜掉你的眼睛、打斷你的狗腿!”
“哼,我說,你還有完沒完啊,”
黃臉老婆沖著滿嘴泛著唾沫星子的周大驢嚷嚷道:“得啦,得啦,別講瞭,耳朵都聽出硬繭來瞭!”
“我樂意,操你媽!”
“操你媽!”
“……”
母夜叉伸著長長的脖子,像隻好鬥的母雞似地每罵一句便非常可笑往前湊攏一下,再罵一句再往前湊攏一下,而周大驢亦不甘示弱,他扯著青筋暴起的脖頸,兩個人在屋子中央掐脖抱腰地對峙著,那極其滑稽的場景活象是兩隻狂鬥著的母雞和公雞,而周扒皮對此卻視而不見,若無其事地繼續埋頭囫圇吞棗。
“操你媽!”
“……”
“行啦,行啦,你們有完還是沒完啊!”
周大驢的大女兒,一個已經上中學的女孩子在旁邊極不耐煩地嚷嚷起來。
“關你屁事,一邊去,滾!”
周大驢又將鋒芒轉向瞭女兒:“操你媽!”
“操你媽!”
被周大驢無端侮罵的大女兒索性亦加入到父母的對罵大陣之中。
“操你媽!”
“……”
卡斯特羅與周大驢兩傢因爭奪廁所的使用權而展開的曠日持久的大戰,其結局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
最終,搬傢的並不是人們想像之中的卡斯特羅,而是周大驢,他們搬遷到新建成的宿舍樓裡。
搬傢那天,非常會過日子的“大罪犯”任何物品也舍不得拋棄:“破傢值萬貫啊!”
黃臉婆一邊翻騰著那些毫無頭緒,亂七八糟的破東爛西,臭巴嘴裡一邊振振有詞地嘟囔著。
經過一番昏天黑的窮折騰,終於將那一堆堆散發著臭氣的、已經徹底黴爛的破爛裝上瞭汽車。
臨走之時,一次也沒有邁進過我傢大門的“大罪犯”面目可憎的黃臉婆突然令我意外地光臨寒舍,讓我不禁目瞪口呆。
她臉上堆著虛偽的微笑,和顏悅色地向媽媽說道:“×老師,我們傢要搬走瞭!”
“是啊,”
媽媽亦是現出一副虛情假意地樣子漫不經心地附和道:“是啊,是啊,在一條走廓裡住瞭這麼多年!真的要走瞭還挺想的呢!”
“是啊,我也有同感啊!”
“大罪犯”黃臉婆繼續說道:“×老師,你看,我有這麼一件事,我在走廊裡搭的那個小個棚子挺好的,能裝不少東西呢,要是就這麼拆瞭,怪可惜的,我突然想到瞭你,我想,你一定能用得著的!”
“哦!”
我和媽媽終於明白瞭黃臉婆此番造訪寒舍的真實目的,媽媽爽快地詢問道:“行啊,那就給我吧,你想要多少錢呢?”
“五塊,五塊錢,×老師,你看你能出多少錢呢!”
“行”媽媽根本沒有跟“大罪犯”討價還價,而是非常麻利地掏出五塊錢,遞到黃臉婆的面前:“沒說的,住瞭這麼多年的鄰居,怎麼好意思跟你講價吶,你要多少,我給多少,……”
“謝謝,謝謝!”
黃臉婆非常滿意地接過五塊錢,然後把一枚鑰匙遞給瞭媽媽:“×老師,這是小棚子的鑰匙,裡面的東西我都搬空瞭,小棚子現在就歸你啦,你現在就可以使用它啦!”
說完,“大罪犯”、黃臉婆揣著媽媽的五塊錢,心滿意足地溜出我傢。
新建的宿舍樓地處偏僻,商業蕭條,蔬菜、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長期居高不下,且品種單調。
極其精明、窮於算計的“大罪犯”、黃臉婆便不辭辛勞地騎著自行車跑出很遠很遠,去她認為商品價格比較便宜的市場采購各種生活物品。
一次,滿載而歸的“大罪犯”在回傢的途中不幸被一輛迎面駛來的小轎車撞得騰空躍起,母豬般的身體從轎車前面飛拋出去,然後,又重重地摔落在轎車的尾部,腦袋撞在馬路邊的條石上,頓時腦漿迸裂,當場氣絕身亡。
而重病纏身、命若懸絲的李湘媽媽居然奇跡般地康復瞭,至今仍健康地,但卻不是快樂地生活著。
“怎麼回事,嗯,這是怎麼回事,”
頭破血流的李奇終於將單位的老書記找來,一進走廊,德高望眾的老書記便解勸起來:“不要吵瞭,不要吵瞭,大傢都消消氣,啊,有話好好說,啊,走,你們都跟我進屋去,咱們和和氣氣地談一談,……”
“哎喲,”
看到老書記走來,始終在門後窺探著的媽媽立刻打開瞭房門,無比討好地跟老書記打著招呼:“書記來瞭,最近身體可好啊!”
“好,好,”
老書記匆匆與媽媽道瞭個寒喧,然後,他沖著兩傢的女主人揮瞭揮手,首先走進李湘傢,見戰事徹底平息下來,媽媽這才走進廚房,繼續忙碌起來。
“哎,”
有人敲門,還有人擊打廚房的玻璃窗:“陸陸,開門啊,快出來玩啊!”
這是鴿子籠裡與我同命運的小鴿子們啪啪啪地又是敲門又是敲窗,邀我出去共同玩耍:“陸陸,快出來玩啊!”
“哎,”
我答應一聲,套上外衣,打開房門,領著仍然淚水漣漣的李湘,興沖沖地與小鴿子們飛到“大黃樓”的走廊裡。
“哎,”
廚房裡的媽媽嘆息道:“唉,這些個勾死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