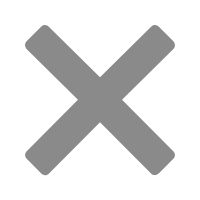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一百三十九章:亂世之兆
我和秦喜跟在劉青山身後,來到薛府的正廳。我的主公大人正在招待五臺寺僧兵團的領頭人,看到我們進來之後,點頭示意。
「韓良,秦兄,你們來瞭。」
薛傢大小姐今天特意打扮瞭一番,濃密的黑發盤在腦後,圓髻前戴著一頂華麗的金絲發冠,上面點綴著乳白色的珠玉。她穿的是上等蜀州雲錦編織成的半臂,輕薄華美的粉紅色佈料上繡著怒放的鮮紅色的牡丹花。半臂下是素白色窄袖短衫與長及地面的飄逸青色褶裙,可以看到精致的鎖骨與修長的頸項下的一片雪肌。
普通的佈料就算很單薄,當其用於制作形式繁復、層次豐富的燕朝貴婦華服時,一整套衣物穿上後也會相當厚實,屬於極為暖和的服飾。然而上等絲綢輕薄細滑,哪怕多層穿下來也不至於會捂得太暖,正適合這種多層疊加的權貴著裝。
當然,以薛槿喬二流高手的深厚內功修為,寒暑不侵,在二十多度的炎炎夏日也足以從容地穿著兩三層棉衣。
她腰板挺直,正襟而坐,儀容無可挑剔,唇邊掛著一絲優雅的笑容,高貴典雅的氣質渾然天成。明明鵝蛋臉輪廓柔和,線條流暢的鼻梁也並不尖刻,按道理來說應該會是個相當親和溫暖的樣子,但細長的月牙眉下,清冷深邃的丹鳳眼似笑非笑,有幾分禮貌的疏離,更有幾分大傢閨秀培養出的雍容大氣,氣質失之溫婉,卻多瞭雪山般的冷冽空靈。正是冰肌玉骨,體態風流的第一等美人。
而薛槿喬對面坐的僧人看起來約莫四十歲上下的樣子,一身土黃色僧袍,濃眉大眼,鼻若懸膽,身材修長,哪怕剃瞭光頭,也是個相貌堂堂,氣質憂鬱的美男子。然而他眼神愁苦,胡茬灰白,額頭皺紋深刻,像是經歷瞭無數苦難和辛酸似的,給人以未老先衰的感覺。
薛槿喬對我介紹道:「韓良,這位是五臺寺的宗勤前輩,乃是圓奕主持的師侄,青州白道的武林前輩,堂堂的一流高手,江湖尊稱『悲苦頭陀』,這次帶隊前來支援青州戰事。前輩,這是我的幕僚,龍頭幫弟子,秦喜先生和唐禹仁的好友,韓良。」
「秦師妹,龐師兄與貧僧素有交集,若不介意的話,喚貧僧一句師叔便好瞭。」
「那我就不客氣瞭,謝謝師叔。師叔叫我一聲槿喬或者小薛即可。」
宗勤慈祥地笑瞭笑,站起身來對我雙掌合十道,「阿彌陀佛,秦施主在敝寺療養時,提過韓施主的名諱與事跡,貧僧有禮瞭。」
我回禮道:「大師幸會,叫我小韓就好。多謝五臺寺的諸位伸出援手。」
我們寒暄瞭幾句後,薛槿喬正色道:「不知五臺寺是否知曉最近的戰況。實不相瞞,青州的戰事十分危險,若是叛軍攻下濮陽,站穩跟腳,則必定會企圖斷掉商丘與汴梁的通路。哪怕汴梁水陸通行無阻,面對成瞭犄角之勢的濮陽與商丘,陷入危機亦隻是時間問題。貴寺派來的人手不僅是戰力還是醫術,都是能解前線燃眉之急的援助。就是不知尚有餘地,還是愛莫能助?」
宗勤眉頭緊鎖,答道:「貧僧亦與住持談過青州的戰事。五臺寺雖然在青州府內,寺內的弟子卻向冀州與鎮南撥去瞭大半人手,如今這支僧兵已是宗字輩與真字輩最後剩下的人馬瞭。隻是,貧僧在來路上觀汴梁駐軍動靜,似乎不像準備即刻援助濮陽的樣子?」
薛槿喬臉上露出幾分不悅之色說道:「師叔的觀察沒錯,正是如此。田煒將軍在此地統籌全府戰事,但對於濮陽的形勢,青州軍部則分化為兩派。我等主戰,若是能在十日內調出兵馬增援濮陽,或許能內外夾擊,挫叛軍鋒芒使其退去。哪怕隻是讓其無法合圍,也足以讓城內的軍民喘口氣。」
「然而軍中的『穩重』派則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必須守好汴梁,確保青州糧草暢通無阻。哪怕要犧牲濮陽,若能夠拉長叛軍的戰線消耗他們的補給和人力,便是戰略上的勝利。」
我和秦喜不禁同時搖頭。這種想法若是在冀州或者西涼這種農耕相對難以發展,耕地不廣的地方還有幾分道理,但是在富饒肥沃的青州土地上,若是能在九月底前攻破濮陽,那萬頃良田的莊稼便能成為叛軍攻打青州最牢固的根基。
軍部的參謀都不是傻子,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依舊如此力爭,怕還是源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畢竟已經有幾十年沒打過這個規模的仗瞭,誰也難以判斷局勢。
宗勤閉上眼睛,沉吟瞭片刻後,沉聲說道:「貧僧不懂兵法戰策,凡事但以田將軍之令為重。但本寺除瞭官府點名的僧兵與醫者外,此行亦是攜帶瞭不少尚未在祠部掛號頒發度牒的弟子。槿喬既是此行的領導人之一,這些多出來的比丘便任由差遣。」
聽瞭此言,我忍不住暗自點頭。宗勤雖然表面上不得不完全聽從軍方調派,但私底下明顯是與我們一派的,將五臺寺多出來的人手都交給薛槿喬管瞭。
燕朝的祠部負責管理僧道等出傢人士,沒有度牒不能當官府認可的出傢人。開國時這個制度是執行得比較嚴格的,任何正式受戒或者出傢修行的人士都得去官府註冊,並且通過瞭官方認證後才能獲得度牒,進行宗教方面的活動。後來這個制度隨著基層執行力的下降,也逐漸成瞭相當寬松的要求。
除瞭宗勤這種名傳江湖,輩份頗高,或是手握寺內實權的和尚必須去獲得官方認可之外,大部分的普通五臺寺弟子,與其他小山小廟的道士僧人都習慣瞭「無證上崗」的做法。而官府雖然對這種情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畢竟這種制度的原本目標便是為瞭提防有人借著出傢的由頭募集私兵。所以聽從官府宣召的堂堂僧兵團雖然能順手帶上一批在官方沒有正式登記的空白人士,但這種弟子輩的存在肯定是需要宗勤背書的,萬一出瞭什麼差錯便拿你是問。也因此,宗勤能夠將其交給薛槿喬定奪行動,實在是一種沉甸甸的信任。
宗勤又問瞭幾個關於青州戰事的問題,低頭思考瞭一陣後,有些疑惑地問道:「槿喬可有派中長輩在此?昆侖乃是大燕武林的領袖,承陛下之命而行,哪怕在戰爭期間需聽從軍部命令,亦有一定的自主權。你是這代的大弟子,但畢竟是弟子輩,資歷想來會有人質疑。若是冷玉仙使在此,吾等的主張亦將不得不被重視。」
薛槿喬的師父是昆侖派長老,一流高手冷玉仙使秦宓。秦宓是京城秦傢傢主的親妹妹,而且自己還是大燕朝廷的四品都指揮使,貨真價實的金枝玉葉。除瞭晉身先天或者封爵之外,已經位處女子身在這個封建王朝能所達到的頂級層次瞭。
除瞭這幾層身份之外,她還是浪裡挑花李天麟最看重的師妹。有著這對大燕前五硬的拳頭背書,任誰都得對她多出幾分禮貌。
薛槿喬苦笑道:「李師叔與數個派中長輩坐鎮冀州戰線,傢師目前在燕州照看朝廷內事,剩餘的派中長老都在鎮南或順安邊界附近。濮陽勢危隻是七月才惡化至如今的地步,因此之前暫無本派長老。龐師伯處理完鎮南的事務便會趕來,但九月之前是無法抽身的。圓奕住持特意囑咐師叔領隊,恐怕也有這層考量。」
宗勤長嘆一聲:「無論是戰局統籌,醫術,武功,甚至經營俗務,貧僧都不是諸位師兄弟中最適合此行的人選,然而住持卻沒有選他們,想來已經是考慮到這點瞭。我佛慈悲,若此層關系能幫助到青州黎民,也是一份功德。」
雖然兩人的交談有點藏著掖著的意思,但是我也大概猜到宗勤的身份不凡。果然,兩人敲定大概的方針後,宗勤對我友善地笑瞭笑:「小韓也許對我們這老一輩的種種往事不熟悉。貧僧俗名喬如晦,出生於燕州喬傢,乃是當地望族。雖然已出傢十數年,但在常人眼中,血濃於水,這層關系許是仍然有些作用的。」
薛槿喬也說道:「宗勤大師當年是喬傢的天才,是與我師父和李師叔同一輩的青年才俊,入過燕武院進修也在朝中任過官職,哪怕是後來堪破紅塵遁入空門,也有著不容小視的影響力。更不用說他本身就是五臺寺羅漢殿的高僧,堂堂的一流高手,這下我們這方總算也有軍部必須重視的人物瞭。」
「好瞭,正事談完瞭,師叔與秦兄,我們準備瞭一席齋飯,若不嫌棄的話,請留下來共餐一番。」
我們一起享用瞭薛府大廚精心準備的素齋。油燜春筍,千頁豆腐,銀耳蓮子羹,紅燒芋頭,甚至還有一道連我自己都做過的羅漢齋。但是與我隨便添加食材的做法不同,這道羅漢齋聚集瞭三菇、六耳、九筍,是真正的「上素」或者「上齋」。宗勤大師雖然對這餐齋飯的味道贊不絕口,但是心事重重,並沒有吃太多。
我對素齋沒什麼感覺,但看著這一桌色香味俱全,精細烹飪的菜肴,看到那擇菜堪稱苛刻,卻在這場戰爭中仍然能夠被精心準備出來的華麗羅漢齋,再想起今早看到的劉姓母女,心裡也有些不是滋味。
用膳後,薛槿喬吩咐我去幫助宗勤和秦喜安頓僧兵團。汴梁有數個大寺廟,大部分的五臺寺僧人都在其中最大的燕來寺裡掛號借宿,還有幾個直接住進瞭城外的營帳幫忙迎接災民,處理傷病。
我們橫跨小半個汴梁後,剛過午時,看到瞭成群的流民和乞丐團聚在鬧市街頭,等著領粥。大部分粥棚是官府籌備的,還有數傢是本地的富豪、望族組織的,而在燕來寺也聚瞭大群人們,這裡的僧人們每日都會免費發粥,診療病人。
秦喜忍不住問道:「這些難道都是被戰事逼迫離傢的人?」
我微微點頭道:「大部分是的。六月叛軍全面侵犯青州那陣,每日都可以見到新的避難流落至此的百姓,但七月濮陽被圍之後,情形一下子嚴重瞭許多,如今官府為瞭安撫這成千上萬的流民已經快忙不開來瞭。」
宗勤默默地領我們進瞭古樸恢弘的燕來寺後,嘆氣道:「阿彌陀佛,哪怕是為瞭這些前程未卜的人們,吾等也要盡力幫助濮陽排除叛軍。軍部的大人們或許耗得起,但這些苦命人實在是等不起瞭啊。」
整個下午我都幫著僧兵團入駐燕來寺和軍營,交接各種文書和信令。在寺裡忙活完之後,正準備回傢,突然發現秦喜招招手準備告別的樣子。
「嗯?秦兄不來我傢吃頓飯麼?剛好認識一下我的媳婦。我記得你說你吃齋已經吃得受不瞭瞭啊。」
秦喜失笑道:「倒也沒有那麼慘,但是大部分的這些五臺寺兄弟們都是好幾年來第一次下山。別看這些大和尚們武功練得紮實,其實都有些怕生呢,我怕是得留下來看著他們。禹仁不是還沒回來嗎?等他回城瞭,我們三人再拜訪你和弟妹,好好喝一晚,如何?」
我與秦喜擊掌道:「一言為定!」
回到傢後,梁清漓和小玉正在廚房裡忙活。我洗瞭手之後也去幫忙,很快便將晚飯做好瞭。
擺好桌子後,梁清漓問道:「夫君可是見到瞭薛小姐所說的熟人?」
我笑道:「見到瞭,還記得我跟你提過的玄蛟衛秦喜嗎?跟我和禹仁大戰聞香散人的那個夥伴,原來這次來的就是他。說起來,我本該猜到的,他當初離開懷化之後,便是去瞭五臺山尋找高僧的醫療。看來恢復得比我想象中還好,當初他可是幾乎一身武功盡廢的。」
梁清漓支著下頜說道:「夫君偶爾會與唐大哥說起這一戰,單單是看見夫君與唐大哥的傷痕,便想象得到那一天的慘烈。」
我回憶起那一戰,想起瞭那份見到夥伴傷殘時的深沉絕望與怒火,想起瞭聞香散人哪怕已經死去,卻仍然會在睡夢中浮現的猙獰笑容,腹部從未消去的痛楚忽然加劇瞭。
我臉上的笑意淡去,揉瞭揉眉心道:「是啊,我似乎從來沒有從頭到尾對你描述過那次遭遇的全貌。也許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尚未走出那一天的陰影吧。」
這時,我的手被一陣溫熱的細膩包裹住。梁清漓雙手捧著我的左手,柔和的眼光中滿是關懷:「奴傢失言瞭,若夫君不想說……」
「不,把話說出來其實是件好事。」我牽著她的手,鄭重地說道,「把所有傷心的,痛苦的,憎恨的東西都藏在心裡,從來不對任何人說出來,其實是很不健康的。嗯,道理是這樣說的,但我也經常犯這樣的錯。你們是我的傢人,所以我也不該顧忌對你們暴露自己的脆弱之處。相對的,我也希望在你們悲傷,痛苦,迷惘的時候,也能夠將這些情緒與我分享,讓心裡更好受。」
小玉這時候站起身來,跑到我身旁給瞭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韓大哥,你對我說的那些道理雖然我記得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忘不瞭的,那就是我和小姐可以永遠都依賴你。所以反過來也是一樣的,你也要依賴我們啊,哪怕隻是跟我們說一些壓抑得很辛苦的話也可以。」
我拍瞭拍小玉的背脊,欣慰地笑瞭:「小玉真的長大瞭。是的,哪怕是為瞭讓你們有個提防,我也應該更仔細地說起這些青蓮教有關的事。」
於是我就著晚飯仔細地將懷化郊外,我們三人對戰聞香散人那天的遭遇重述瞭一遍。小玉就不用說瞭,雖然在我和梁清漓的督促之下已經學習瞭一年的武功,但是從未接觸過這種江湖廝殺,聽得口瞪目呆。梁清漓雖然見多瞭人心叵測與世態炎涼,卻對於這種赤裸裸的血腥爭鬥沒有直接的認知,隻是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掌,臉色有些蒼白。
「……結果你們也知道的。雖然我們勝瞭,但是代價實在是有些沉重。禹仁失瞭一臂,我武功盡廢,差點半身不遂,秦喜則是連連催發精血秘術,內府、壽元受損,一身武功失瞭八九。現在看來,五臺山的大師們醫術果然夠高超,秦喜若不是確實恢復瞭大部分功力,是絕對不會前來當累贅的。」
我看到兩女的臉色,溫言道:「我不是想要嚇你們。若是可能的話,我隻想自己去面對這些殘酷的戰鬥。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如今離亂世也隻有一線之差而已,而這個世道對女性比男性還要殘忍。也許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需要為瞭生存,為瞭性命去搏鬥。在那之前,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和汗水,也許就能在最需要的時刻,救你一命。」
兩人臉色各異,但都若有所思。江湖、武林、戰爭已經成為瞭將會主導整個天下的主題。哪怕再不情願,我們也得讓自己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天晚上,我們就寢後,梁清漓依在我的懷裡輕輕地摩挲著我的胸膛,低聲問道:「夫君,奴傢的武功在你看來,有多強?」
「單憑內功底子和拳腳功夫的話,你應該已經有三流高手的水平吧。不過真正的廝殺和戰鬥中,這種人為劃分的層次隻是最淺顯的分類方式。」我想瞭想後,如此解釋道,「而且你滿打滿算才習武兩年而已,能夠達到這個進展已經堪稱神速瞭。不少人窮其一生都無法躋身這個層次呢。」
梁清漓有些憂鬱地嘆道:「夫君與師父都說奴傢有習武天賦,但奴傢習武已有兩年瞭,期間戰戰兢兢未敢松懈,卻隻是堪堪進入三流之境。這份微薄的力量,又能有什麼用處?」
我撫著她柔順的發絲,沉吟道:「話不能這麼說。按照道理來說,我和禹仁、秦喜三人是肯定無法殺死聞香散人這個級別的高手的,但是現實與理論不一樣。在絕大部分的戰鬥中,堅強的意志,靈活的腦袋,還有見機行事,隨機應變的能力,依我所見,都比內功修為和招式的熟悉更重要。『實力』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是你手無縛雞之力卻每次都有辦法對付一流高手,那你也是一流高手。」
「我的初衷是為瞭讓你和小玉能夠盡量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大燕,武功是掌握命運見效最快的方法。但比起讓你為瞭這些東西煩惱,並且逼迫自己練武變強,我更寧願你心態放寬些,不要壓力太大瞭。被這些執念所控,那就是入瞭魔道瞭,也許會得不償失。」
懷裡的愛侶沒有言語,隻是十指交叉地握住我的手,淡淡的鼻息撓在我的肩頸。
良久後,梁清漓抬頭看著我,清澈的雙眸凝重而堅決,一字一句地說道:「夫君一直想要為奴傢與小玉遮掩江湖的殘酷與世道的艱苦,但現在奴傢可以幫助夫君去負擔那些沉重的職責瞭。」
「不僅如此,以後,輪到奴傢來保護夫君,保護這個傢瞭。隻要能做到這點,無論是墮入魔道還是修羅道,奴傢都不在乎。」
我心中被無邊的溫暖填充,沒再去試圖對她說什麼正道,什麼執念的大道理,甚至沒有試圖去打消她主動承擔這種危險負擔的想法,隻是摟著她笑道:「能有一個互相扶持的伴侶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啊。謝謝你,清漓,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
梁清漓抿唇吻瞭吻我,也笑瞭:「夫君,也許這便是師父的感受吧,奴傢忽然有些理解她為何能夠如此堅定於自己的道路瞭,因為她也有自己想要守護之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