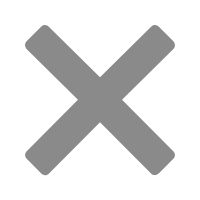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一百七十四章:坦誠相對
我思考瞭一天一夜之後,終於做好瞭心理準備,在預計抵達黃土林的前一晚與梁清漓在營帳中交談。
這天晚上,哪怕沒有任何人催促我,愛人也沒有任何不對的跡象,一切都平和且安寧,我的心臟仍然不爭氣地猛烈跳動著,仿佛掛瞭無比沉重的負擔。沒來由地,我突然想起瞭很多年前,仍是個孩童的我不小心將老師帶來課堂的一臺投影儀打碎瞭。那是一臺能夠在天花板上投射出星空的昂貴儀器,被我在內的數個學生們爭著操控。然而輪到我時,我卻失手將它碰到地上摔壞瞭。
我仍然記得那時的我手足無措的惶恐,和那無與倫比的罪惡感。哪怕知道自己該誠實地對老師說出事實並且道歉,然後勇敢地直面懲罰,從某種層面來說,我也寧願當場從三樓的窗戶跳出去,而不是面對自己的錯誤。
那個孩童時的沉重感與此時的我所感受到的煎熬如出一轍。那是對梁清漓會如何反應的擔憂,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負罪感,和受刑的罪犯即一樣,對未知的未來與自己所要承受的後果的本能恐懼與焦慮。
營帳裡亮著一盞油燈,而梁清漓坐在馬紮上輕輕地梳著頭發。
黃土林之戰結束後,我們終於能洗去易容,以本來面目示人。過去一個多月裡,我隻有寥寥幾次能夠見到伴侶的容顏,所以此刻看著她真實的臉龐時,竟有些久違與陌生。
梁清漓心情頗佳地哼著小曲,而我隻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她梳發,不由自主地想起瞭與她初遇時的模樣。
清漓精致的瓜子臉蛋比起一開始遇見她時圓潤瞭一分,兩道細長的娥眉如月牙兒,為她秀美的容貌添瞭恰好到處的婉麗。相信任何見到此時的她的人都能贊同,這是一個十分符合東方婉約美的古典佳人。但作為一個在兩年前便認識她的人,若要說起梁清漓身上最大的變化,那一定是她的眼眸與氣質。
在聚香苑時的她,眼神十分柔順,並且很多時候會帶有經過嚴苛禮儀訓練培養出來的禮貌笑意,充分地發揮出她溫婉的氣質優勢來,親和中帶著若即若離的距離感。但這份點到為止的儀容總會有些為瞭迎合某種形象,某種目的的刻意。也許能夠稱之為世故,也許能稱之為老練。
而此時的她不再需要去討好什麼人,去維持什麼形象,於是那些多餘的掩飾被褪下,洗凈瞭。以往那種用心顯示出來的矜持與刻意不再,留下的是溫潤大方的光彩,純粹而自然。而修習瞭武功,明晰瞭自己的道路與堅持之後,梁清漓身上那纖弱的氣質也消退瞭,溫柔秀麗依舊,但表面之下的寧靜沉凝似水。
梁清漓註意到的我的目光,微笑道:「夫君在看什麼呢?」
「當然是看你啊。好久沒有見到你的容顏瞭,我十分想念呢。」
梁清漓親昵地將手指撫過我的臉龐道:「奴傢也是許久未見過夫君的面容瞭,還是看著這張臉心安。」
我被她輕輕的動作激得縮瞭縮肩,問道:「這幾天各種大事不斷,我都有些跟不上節奏瞭。你還好吧?」
「奴傢一直隻在邊上觀望,真正危險的事物都是夫君等人去做瞭,最多隻是擔憂結果,何談不好?」梁清漓有些幽怨地答道。
「抱歉,抱歉,我實在是沒有辦法讓自己帶你進入那麼危險的場合。」我雙掌合十抱歉道。
「不,夫君不必為此道歉,是奴傢任性瞭。若奴傢真的執意跟上去瞭,也許隻會釀成大錯。幸虧薛小姐當時趕瞭過來,否則……」梁清漓露出瞭後怕的神色,雙手下意識地緊緊攥住衣角,「薛小姐實在是奴傢與夫君的大恩人,不但救瞭夫君,也讓奴傢有機會為梁傢申冤。」
「嗯……不過這次我們直上燕京,恐怕有好一陣子沒法見到小玉瞭,我有些放不下心來。」
梁清漓有些擔憂地說道:「嗯,奴傢也是,不過薛小姐與奴傢說不必擔心,府上會把她當自傢人照顧的。」
我問道:「聽薛槿喬的說法,好像你們倆個談過瞭梁傢的事瞭?」
「嗯,黃土林之戰那晚,薛小姐尋到奴傢之後,與奴傢聊瞭許久。她十分義憤,讓奴傢都有些驚訝,但也很感激她為奴傢著想的心意。她雖然嘴上不說,但跟奴傢一樣擔心你的傷勢。」梁清漓回憶起那晚的事娓娓道來。
我嘆道:「我的傷勢算不上什麼,秦喜和景伊的傷勢才真的令人擔心。還有孫倩,與那些犧牲性命的士兵……」
說起孫倩,我們一時都默然瞭。還是梁清漓打破瞭沉默問道:「夫君,你到底是如何與秦大哥兩人對上右護法這種高手的?奴傢雖然見識短淺,但也明白那是什麼樣的人物。便是師父,也不可能在右護法手下撐過三十回合。兩年間從一個身無武功的尋常男子,到能夠與一流高手過招的強者,連六大派也少有這樣的天才。」
我聽到這話,正色道:「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之前與你說過的符籙。之前,我沒有對你透露符法的來歷,因為我不想讓你分心,現在事情告一段落,你有什麼問題盡管問吧,我不會再對你隱瞞瞭。」
梁清漓咬瞭咬嘴唇,直直地看著我問道:「夫君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韓良,是建南饑荒中逃到順安的孤兒,是在越城與你不期而遇的龍頭幫小卒,是你心愛的夫君,也是……一個擁有一些不屬於此界的知識的人。」
既然開瞭頭,那就不必再遮遮掩掩的瞭。我一口氣說道:「你有沒有想象過,我們所生長的這片天地並不是世間唯一存在的天地?其實在天之外有著比漫天星星還要多的異域,是不在此,不在彼,不在任何能憑著眼睛或者五感觀察到的,遙不可及的天地。」
梁清漓瞇起眼睛,似乎想要在腦中描摹出那樣的光景,最後遲疑地說道:「夫君是說,像妖精,仙人,還有鬼魂精怪居住的地方那樣?與凡間隔絕的國度?」
「嗯,可以這麼理解,但還要更遠,更難以觸碰。在那些千千萬萬的異域裡,有適宜人們生長的地方,而有些地方的居民是你熟知的仙人,鬼魂,更多的地方卻是居住著跟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生長在無數片與大燕截然不同的大地上,穿著和我們不同的衣物,有著跟我們不同的習俗,但跟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若知道你我,知道大燕的存在,看我們便會跟我們看他們一樣,如水中月,鏡中花。甚至連時間對於這種異域都是不同的,有些國度存在於過去裡,尚未來到如大燕這般繁昌的時代,有些卻存在於遙遠的未來裡,比我們領先瞭千百年,所有人都過著大燕子民難以想象的發達生活。」
「天上一日,人間十年麼。」梁清漓喃喃說道。
「哈哈,也許吧。隻不過,他們的天空與人間,都會是與我們不一樣的,這可比仙凡之隔還要劇烈。」我躊躇瞭幾秒後,繼續道,「我的意思是,從你認識我到現在,我身上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都是因此而來。我知道你從一開始便註意到瞭,並且一定有很多疑問。為何我這樣一個小夥子會知曉天文地理,歷史算學,還有許許多多根本不符我對你所說的,關於自己來歷的東西。」
「夫君的意思是……」梁清漓反應瞭過來,臉色駭然。
我緩緩地點瞭點頭:「嗯……在你面前這具身體裡的靈魂,並不僅僅是韓二的,它還有一部分來自那天之外,一個完全陌生於大燕的國度。因此我一個目不識丁的普通小子,才能有你熟知的諸多能耐和學識。」
梁清漓像是在看什麼陌生的人,又像是有些瞭然,伸出手來摸瞭摸我的臉頰:「奴傢曾經聽說過,有些天生神童三歲吟詩七歲做文章,便是因為前世的記憶在這一生被帶過來瞭,是有宿慧的人。這……跟夫君有些相似吧?」
「呃,從效果上來看,也差不多吧。隻不過這種故事裡,帶有宿慧轉生的神童是一生下來就記得前生之事,但我是三年前才腦袋裡多瞭這份來自天外天的靈魂與記憶。像是這符籙,你也應該猜得到,屬於整個大燕都罕見的能耐。太清道貴為國教,我都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類似的法門。這是不屬於此界的知識與力量。」
我猶豫瞭片刻後,還是將最關鍵的一部分道來瞭:「而且,我不隻是個獲得瞭天外知識的幸運兒,而是真真正正地融合瞭兩個人的靈魂。在這個軀殼裡,是大燕的韓二與一個來自天外天,名為『周銘』的陌生人合二為一的存在。韓二的父母和傢人所認識的那個『韓二』,已經不在瞭,在我遇到你之前,在『周銘』這個天外天旅客降臨的那一刻,韓二便永遠地不見瞭。」
聽到這話,梁清漓若有所思地答道:「若奴傢認識『韓二』,那一定會為此感到悲傷。不過……奴傢從來都隻認識這個全新的夫君。比起悲傷,更多是好奇。你為何突然要對奴傢說這些事呢?且不說奴傢隻是個見識短淺的小女子,無論是再有見識、智慧的人,聽到這番話都很難相信吧?更何況,若夫君體內真的有著異於中原人的靈魂,也會令奴傢很困擾呢。就算奴傢相信瞭,夫君就不怕奴傢無法接受?」
我認真地說道:「因為你是整個大燕裡,不,整個宇宙中,我最重要的人。哪怕事實怪誕得令人難以置信,我也不願對你說謊。也許這是我的任性吧,明明不說出來,也應該對我們之間的關系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我不想要在自己心愛的人面前,還要隱藏真實的自己。哪怕我就是我,從你第一次見到我時,便是如此,而我對你的心意,我們一起經歷過的東西,都沒有半分虛假,我也想要讓你知道關於我的一切。」
梁清漓聽瞭這話,將馬紮移到我身前,握住我的手調侃道:「夫君可真會說好聽的話。這下就算奴傢有遲疑,也不得不接受瞭,不然豈不是讓夫君小瞧瞭奴傢的心意?」
我輕輕地揉著她的手腕,無奈地說道:「你話裡話外,除瞭對我那過於奇異的出身之處顯得很驚奇之外,都好像沒有特別驚訝的樣子。我是不是掩飾得很差勁?感覺是個人都看得出我的背景和表現出來的模樣,完全對不上。」
「嗯,夫君也沒有很用心地去裝作自己是個平凡的人呢,嘻嘻,也許是因為夫君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與奴傢變成這樣的關系吧?不過,無論是誰,看到夫君所做的事,聽聞夫君所講的話,便能夠明白,這絕不是普通的農村小子能夠做到的。隻是,連奴傢也沒有想到,這背後的原因竟會是如此奇特。」梁清漓忍不住笑道。
我說道:「我看得出,其實你不是完全相信瞭,隻是因為我是你夫君,所以才勉強接受瞭。沒關系,我也不準備就此突然變瞭個人。如我所說,你在之前與現在見到的,喜歡上的人,從來就是這個我。隻是現在我能夠在你面前更放肆一點瞭,不必顧忌著掩飾自己腦袋裡那些驚世駭俗的思想。」
「夫君,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想要對奴傢說的,是不?這段時間來,你的心事重重,奴傢原以為是在擔憂叛軍之事,但現在看來,也許還有什麼其他的。」梁清漓柔聲說道。
我坐直身子正視她道:「是的。之前我說瞭,你所認識的韓良是融合瞭韓二和周銘兩個靈魂的人。但作為天外天的旅客,周銘能夠邀遊寰宇,去探索那些陌生的,有著天地隔絕的異域。在那個時候,韓良的靈魂是分成兩份的,一份在這個軀殼裡,跟你和大燕的所有人生活,另一份在周銘的軀殼裡,生活在另一個與大燕完全不同的國度裡。」
我在這裡止住瞭,靜靜地等待梁清漓的回復。她似乎被我復雜的講解繞得有些頭腦發昏,讓我掰開來解釋自己的靈魂「分成兩份」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嗯……你知道神話裡,仙人們偶爾起凡心時,會用法術分出一道自己的分身,下放到人世間嬉戲,或者點化有緣人的那些故事嗎?你會說分身就是仙人麼?不完全是吧?但分身便不是仙人麼?好像也不對。韓良便是我在大燕的分身,周銘便是我在天外天的分身。」
梁清漓有些瞭然地說道:「哦,夫君這麼說,奴傢便明白瞭。但聽夫君所說,夫君同時是韓良與周銘兩個人,而韓良是分身,周銘才是夫君真正的本身面目?夫君,你是仙人麼?」
我嘆氣道:「我雖然有些超乎常人的能耐,但離這種神通蓋世的仙傢人物差瞭十萬八千裡。比起分身,每一個『周銘』所降臨的那片天地,都跟主體的我沒有差距,不像故事裡的仙人那麼主次分明。」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我的靈魂是這些不同的國度,不同的人生裡的『我』聚集在一起的東西。在這裡與你說話的是韓良,是大燕的我,但也是周銘。周銘在大燕之外,有著自己的人生,他來自一個叫中國的地方,是中國的我。中國是一片跟大燕有些相似的神州大地,但是處於遙遠的未來,是一個比大燕還要晚千年的地方。『周銘』能夠在不同的異域間旅行,然後正是來到這方天地後,成為瞭大燕的我。」
梁清漓閉眼揉瞭揉額角,原本已經有些放松的神情又一次繃緊。一陣令我心臟狂跳的沉默後,她緩聲問道:「那麼夫君到底是『韓良』,還是『周銘』呢?對奴傢來說,這許是唯一有價值的問題。」
「都是,但也不完全是。」
我想瞭想,將這些時日來,對於自己的經歷的一些疑惑與思考,和思考後的結論對她,也是對自己解釋道:「佛傢的道理你也有所瞭解吧?超脫於時間和寰宇,肉身皮囊,剝離瞭一層層虛妄之後,留下的最純粹的東西,便是『我』的本性。這份本性在大燕,便成瞭韓良。在天外天的『中國』,便成瞭周銘。」
「雖然兩者會有些表面上的不同,但這都是在紅塵中因緣際會而生,因緣離散而滅的色相。真正屬於我的本質,無論時間地點,無論貧富善惡,都不會有所改變。所以,韓良是我,周銘也是我,我是他們,但也不止是他們。就如你是梁清漓,梁清漓也是你,但真正的你也不止於此那樣。若這一生是修行,那我們便是在尋找,在挖掘這份本性。」
若將穿梭時空的經歷當成色界的緣生緣滅,那我在其中的掙紮和煎熬,便是屬於我自己的業報。明晰自己的內心與真實的意願,是修行,也是明心見性的道路。金剛經有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也許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我痛苦於自己的心意和對戀人的辜負,隻是落入瞭我執的陷阱裡而已。
但我畢竟不是佛教子弟,我想縱情地去愛,去恨,去體驗心中最真實,最誠摯的情感,想要找到俗世的解決方式而不想要將這些對自己重要的東西「放下」。甚至,我不願割舍這份自己為難自己的爭鬥,因為放下瞭這自我矛盾的糾結,我便缺失瞭自己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這樣的「放不下」或許能稱之為執念。但,如果去除瞭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去除瞭色相香味觸法這六識,還是固執地想要去尋找這樣與自己和解的答案,那麼這份願望的力量,或許能算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本性瞭。
梁清漓嘟嘴道:「夫君在飛龍寺待瞭小半年,說的話也跟大和尚們一樣瞭。奴傢資質愚鈍,隻是一知半解而已。」
「是麼?我倒覺得你似乎頗有體會的樣子呢。」
梁清漓輕聲說道:「奴傢是這樣的理解的。眼前的夫君便是真實不虛的夫君,以前是,以後也會是。更多的,便是庸人自擾的煩惱。」
「嗯,沒錯。」我微笑道,「或許還能加上這麼一份體悟:無論是在哪個國度,在哪片天空下,你遇到的,總會是真正的我。而遇上瞭你的我,也每次都會為你傾心的。」
「夫君本不必對奴傢說這麼多的。不僅是為瞭奴傢,甚至為瞭夫君自己,如今奴傢知道瞭,便無法不去思慮,去疑問。這樣,真的比保留這些小小的心思,更好嗎?就算不對奴傢明言一切,奴傢也相信夫君的愛是真實的。而這對奴傢便夠瞭。」梁清漓抿唇問道。
我滿臉歉意地說道:「對不起。因為我很自私,也因為對愛人保留這麼多關於自己的心思,實在是一種很難受的負擔。這也許是一種奢望,但我一直想要有一個無論如何都能與之分享自己的心思經歷,在見到我所有的好與壞之後,仍然接受這一切的人。我希望你是那樣的人,清漓,我也希望自己能夠為你成為那樣的伴侶。但這也是個很苛刻,很理想化的要求,所以我這麼擅自坦白,隻為瞭自己心裡能夠卸下負擔,其實是一種極為自私的行徑。」
梁清漓若有所思地說道:「自私麼?也許吧,但……奴傢卻覺得這種徹底袒露心聲的行為,很棒呢。」
「其實這還不是最自私的。」我停頓瞭一陣後,萬分艱難地說道:「……在第一次異域之旅時,『周銘』來到瞭大燕,成為瞭『韓良』遇上瞭你,與你結成愛侶。但是在那之後,我又進行瞭一次異域之旅。我去瞭一個在遙遠的未來裡,處於極西之地,名為西聯的地方,在那裡,我成為瞭一個叫做楊凌雲的男子,遇上瞭西聯的兩個女子。然後……對她們動心瞭。」
「我不想對你隱瞞這件事,所以在此對你坦白交代。無論是韓良、周銘、還是楊凌雲,從本質上,終歸都是我。哪怕在遙遠的天外天,借用著屬於楊凌雲的軀殼,我也是我,沒能保持忠誠的心。對不起,我背叛瞭你的信任。」
比起天外天的旅客,異域的靈魂,這才是真正讓我難以啟齒的自白。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臉色是什麼樣的,滾燙的臉龐交雜著羞愧,糾結,自我厭惡,和遲疑,應該很難看吧。我在說這話時,甚至有些不敢直視戀人的雙眼,但還是硬著頭皮將一切都交代瞭。
梁清漓沒有立刻回答。她的神色復雜而難以琢磨,但我清清楚楚地從她臉上捕捉到瞭令我的心一沉到底的難以置信與難過。
我令她失望瞭。
我……對不起她瞭。
哪怕是聞香散人將我打得半殘的拳掌,與過去一年的傷病折磨,都比不上這份醒悟所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失落。哪怕她能夠諒解,或者接受,我們之間的感情也永遠地被改變瞭,再也無法回到原本的模樣。
有那麼一瞬間,我深深地後悔自己執著於這些該死的原則的性格。明明閉上嘴,不去想,不去糾結這些復雜的經歷與心思就是瞭,那樣我與她都能免於情傷,為何要多此一舉地彼此傷害?而比起這個,我更憎恨自己不受控制的心,為何不能就滿足於已經擁有的美好,為何明明自私地渴求另外的人,卻又糾結於自己的那些原則,難以抉擇,無法徹底地斷絕這些念想,而是貪婪地想要魚與熊掌兼得,滿足自己對於道德感與愛情的追求。
但這終究隻是在逃避責任。這顆心是自己的,所想所做的,也都是自己的,所謂不受控制的心,也不過是個面對被自己傷害的愛人時,蒼白空洞的借口而已。無論如何,我都無法不對這個自己平生最愛的女子,誠實地,徹底地,給予她作為我的伴侶應得的真相。
然後承受代價。
我堅定住自己,幾乎要蹦出胸膛的心臟響到填充瞭突然安靜下來的營帳,在難熬的沉默中等待著她的審判。
許久,許久後,梁清漓面無表情地問道:「她們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澀聲答道:「按照大燕的認知,她們是來自西域以西的人,一個金發碧眼,另一個有著琥珀色的眸子,兩人都很溫柔,也很美麗。」
打開瞭話匣子之後,我繼續說瞭下去,將自己在西聯的經歷,與倆位紅顏知己相識相交的過程簡略地描述瞭一遍。
梁清漓眉頭輕蹙,一直緊緊地盯著我:「奴傢明白瞭……確實很有夫君的風格呢。你說你準備接受『艾莉克希絲』,那麼你準備在那片異域裡與她們在一起麼?」
「我不知道。」我誠實地答道。
「為什麼?」梁清漓有些疑惑,「郎有情,妾亦有意,為何不更進一步?」
我垂下頭道:「對那個名為奧麗維婭的女子,我隻是動念瞭,但並不準備與她發生什麼。而另一個名為艾莉克希絲的女子……我告訴她,我確實喜歡她,就如她喜歡我一樣。但是我請求她給我一些時間,因為我的戀人是你,我無法在對你誠實地訴說一切之前,與她有任何實質的關系。所以,無論是我還是她,都無法知道之後到底會是什麼樣。」
梁清漓露出瞭無法掩飾的驚愕之色:「夫君與她……未曾結合?」
「沒有,我請求她給我一些時間,等待我下定決心。」我苦笑道,「哪怕我的心背叛瞭你,也背叛瞭自己,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自己真正地跨越那條底線的。但這隻是最最低限度的底線。」
戀人仔細地觀看瞭我幾秒後,嘆瞭口氣說道:「……這果真是夫君的作風呢。」
我沒有說話,但是梁清漓的反應卻沒有我想象中那麼猛烈,反而聽瞭我的話之後,有些啼笑皆非的樣子。
仿佛感覺到我的不解和焦慮,梁清漓搖瞭搖我的手臂,柔聲道:「好啦,奴傢乍一聽到這種消息,確實有些晴天霹靂的感覺。但是夫君其實隻是對她們心生仰慕之意而已,並沒有實質地發生關系呢。如此一來,哪怕一下子便出現兩個情敵,奴傢若要怪罪夫君,反而是不完全占理的呢。」
我心情沉重地說道:「發生關系隻是一層遮羞佈而已。我心中明明應該隻有你的,卻還是沒能阻止自己去喜歡上別的人,真正該犯的錯誤,已經犯瞭。」
梁清漓噘起嘴來,難得地不贊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夫君,聖人的道理也有『發乎情,止乎禮』的說法。真要按照夫君如此嚴苛的要求,世上豈不是除瞭聖賢之外,所有人都連想都不能想瞭?便是奴傢也不想如此啊。」
我皺眉道:「好吧,你說得對,我這人確實有點喜歡鉆牛角。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你對另一個男人有瞭同樣的心思,我作為你的伴侶會徹底心碎,痛苦不堪。所以我這樣對待你,何談公平?又何談是個稱職的夫君?你又真的能夠接受這一切,而不傷心麼?怎麼可能?」
「而如果我對你誠實道來之後,又準備回到西聯,跟這個女子談情說愛呢?那樣就徹底打破瞭我作為你的愛人的所有底線瞭。但你也許已經從我的話語中聽出瞭,其實我還在僥幸地希望能有這麼做的機會,甚至希望能夠獲得來自你的許可,讓我能夠心安理得地這麼做,不是麼?」
梁清漓理瞭理肩前的發絲,平靜地看著我說道:「若奴傢不願夫君如此,若奴傢懇求夫君,一心一意地隻與奴傢在一起,無論是在大燕,在中國,還是在什麼遙遠的異域,夫君會答應奴傢嗎?」
「……我曾無數次地設想過這個情景,這個問題,但從未能夠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
我將十指插進頭發,深深地思考,心中前所未有地掙紮。這才是最令我煎熬的選擇。如果我最愛的人要求我保持忠誠,保持作為她的愛人最基本的底線,讓我拒絕艾莉克希絲,拒絕任何可能令我心生好感的對象,比如奧麗維婭,比如……薛槿喬,我做得到麼?
眼前突然浮現瞭自己對艾莉克希絲表示自己已有對象時,她傷心欲絕的面容,又想起她聽到我揭露真相,願意接受她時,金發美人臉上亮起的由衷喜悅。我真的能夠逼著自己斬滅她的期盼,讓她再次露出那個絕望而悲傷的神色嗎?
如此過瞭足足一分鐘後,我才艱難地擠出一句話來:「如果你實在是沒有任何辦法答應的話,我會的,因為這本就是我應該做到的東西。但是在此之前,我會苦苦哀求你,爭取一個能讓我離開大燕時,與那個不是你的女子在一起的機會。」
「這意味著我心裡最真實的意願,其實是會為瞭一己私欲不知廉恥地要求你,要求一個理應獲得我的忠誠的愛人為我犧牲,為我承受心碎。對不起,這是讓我最對自己失望的一個答案,因為它是如此卑鄙與醜惡,卻也如此真誠。」
說出這句話後,我頹然垂首,仿佛聽到內心裡那個堅持至今,卻已然殘破不堪的原則,徹底粉碎的聲音。
我為瞭能有機會成全自己腳踏數條船的戀情,已經跨越瞭所有的底線,不,已經沒有底線瞭。寡廉鮮恥,卑鄙齷齪,自私自利,臭不要臉……若我身邊有一個這樣的男人,哪怕是我關系很好的朋友,我也會瘋狂地搖著他的肩膀,對他痛罵一遭,試圖讓他醒悟這種行為究竟有多麼值得唾棄。
但……這便是我最終的,沒有絲毫虛假的選擇。
在恪守自己的原則、保持對伴侶的忠誠,與腳踏數條船,維持那些讓我的掙紮和努力擁有瞭無法比擬的意義的戀情之間,我終究還是選擇瞭後者。選擇瞭舍棄那些我進入超越空間前自以為無可動搖的堅持與道德感,最終達成瞭這個讓我自慚之餘卻又有些釋然的結論。
我抬起頭來,竭力維持著表面的平靜,對上梁清漓清澈的雙眸,再次發現自己無法讀懂她的情緒。
一陣漫長的,讓我快要窒息的寂靜之後,梁清漓伸出手來,嗔怒地捏著我的臉頰說道:「雖然奴傢早就預料到,以夫君的聰明才智,溫柔體貼,必會使許多女子傾慕,但還是沒想到,最危險的對手會是來自天外天的異域呢。」
她像是揉面團似的,悶聲捏扯瞭幾秒後,改為輕柔地捧住我的臉,感慨地說道:「風流成性,三心二意的人,奴傢見得多瞭,無論是男子還是女子。有很多人曾對奴傢說過,自己之所以三妻四妾,是因為舍不得讓任何對自己重要的人受傷。奴傢向來對此嗤之以鼻,但,若是夫君這麼說的話,奴傢也許真的會相信的。」
「奴傢是第一次見到夫君這般的人,如此為自己的心意痛苦、掙紮,如此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選的道路究竟有什麼代價。因為所有那些其他如此對奴傢解釋的人,都沒有夫君這麼徹底地為愛人設身處地地去體恤,著想,如此誠摯地將他人的感受作為自己的感受……所以,所以奴傢也能體諒夫君的困難呢,因為奴傢也想成為能夠感同身受地為夫君考慮的妻子。」
「何況,奴傢終究是大燕的子民,大丈夫妻妾如雲,其實是一件對奴傢來說天經地義的事呢。也唯有像夫君這樣融合瞭不屬於大燕的靈魂的人,才會對自己本就應當能夠享用的東西如此不安。」
梁清漓有些低落地說道:「奴傢當然想成為夫君唯一的,最愛的伴侶。但奴傢也不想做個自私的女子。不,夫君既然會在遙遠的天之外也過上不屬於韓良的一生,那麼奴傢逼著你在各片異域裡忠於奴傢,哪怕以周銘,以楊凌雲的身份生活時都要封閉內心,那其實……十分殘忍呢。畢竟,奴傢已經占據瞭屬於韓良的一切瞭,不是麼?」
我苦澀地說道:「這一點也不自私,倒不如說,你在這一點自私才是正當的,正確的。我才是自私的那個人,因為我的本性,無論是韓良還是周銘還是楊凌雲的本心,都已容納瞭不止你一個人。盡管……盡管你是我第一個愛上的人,也是我從始至今,最愛的人。哪怕這麼說已經失去意義瞭,但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麗人露出瞭一絲瞭然的笑意,對我眨瞭眨眼睛:「奴傢也毫不懷疑。因為夫君說瞭,能夠為奴傢切斷另外那份關系。以夫君的的溫柔心思與深情,這麼做不亞於斷手斷腳的難受,以此可得,奴傢在夫君心中的地位還是挺靠前的嘛。」
她頓瞭頓,認真地說道:「夫君,你其實沒必要對奴傢說這麼多的。但是你還是這麼做瞭,因為你就是這樣一個人。奴傢可以不在乎你在天外天的異域天地如何,卻不能不在乎的自己眼前,身前的男子,是否仍是當初令奴傢傾心的那個人。而哪怕你告訴瞭奴傢這麼足以令人懷疑一切的事,奴傢卻更加堅信,夫君便是夫君。」
「當初,你身上最令奴傢著迷的便是毫無虛偽的真實與赤誠。」她語氣放緩,溫柔地笑道,「也許夫君說的話讓奴傢有些難過,但除瞭你之外,不會再有第二個人如此赤裸地將自己的所有心思與念想,無論好壞,都袒露給奴傢,不再給自己留下任何辯駁的餘地。所以,不要太難為自己瞭,因為夫君的心意,奴傢感受到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