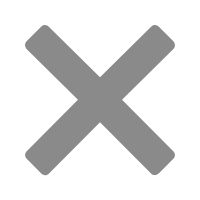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一百七十七章:燕京
又走瞭一周後,路過的村鎮人煙越來越濃稠,官道上的行人說話的腔調也變得與青州和順安截然不同。而我雙臂的傷勢終於恢復到可以將木夾板也脫下來的程度瞭。
在臨近十月底的這天早晨,遙遠的天際終於出現瞭燕京的蹤影。走近瞭點後,我瞇眼看瞭一陣,驚訝地問道:「那條河是直接接引進城瞭?好大的工程。」
唐禹仁點頭道:「沒錯,太祖在此立下國都後,花瞭十年時間開鑿瞭一條接通雁嘴江的水渠,名為『楊水渠』,因兩畔種滿瞭楊柳得其名。」
薛槿喬接著道:「燕京在晉朝時靠著的是彼時的運河與溪谷河兩條水道得水利,但是運河在王朝衰敗時長達數十年戰亂時期間淤塞破敗瞭,溪谷河也因為雁嘴江移道逐漸幹涸。直到楊水渠被建成之後,京城的人口才能夠極大地增長,重現瞭晉國大都的氣象,甚至更甚。」
我們來到足有兩丈高的雄偉城墻下,看到絡繹不絕的馬車、商販,還有成隊的行人排著隊等著進城。
車隊的帶隊軍官顯示瞭文書後,很快便被放行。薛槿喬對唐禹仁說道:「禹仁,你帶著嚴覓去刑部,剩下的這些人不用我們管瞭,自有去處。我會帶韓良他們去薛府安頓,然後得去見師父和去兵部稟報。」
唐禹仁與車隊離開後,薛槿喬領著我們穿梭於車水馬龍的街道中笑道:「怎麼樣,是不是跟越城有幾分相似?單論規模,便是連汴梁也比不上這兩座城市。我們得在京城呆好幾天,你們可以盡情地去遊覽。」
紫光寺內賞佛像,雁歸塔外聽晨鐘,楊水渠畔折柳葉,凌霄觀中上香火,朱雀酒樓嘗珍饈,雁嘴畫舫乘風醉,都是這段時日來薛槿喬提到過的久負盛名的景點與遊玩京城不得不做的事。
梁清漓看著周邊洋溢著旺盛活力的人群道:「燕京好像流民不多。」
「嗯,據我所知,他們很多都被安置在城外的村鎮和郊野的營帳裡,還有少數在白虎區。這裡是朱雀區,自然見不到。」
燕京大大小小的街道和建築被劃分成四個大概的區域,以四象為名。青龍與玄武是最昂貴,最高檔的地段,多是皇室、官宦、與世傢的宅子。朱雀是商業區,人流量最大也最繁華,白虎則是普通居民的住宅區,不過到瞭百年後的如今,哪怕是白虎區的住宅,也不是尋常人買得起的。
在這四個區域之外,京城的最核心之處是皇城,隻有受到準許的臣子才能進入其中參加早朝,也隻有皇室子弟才能在其中居住。
薛槿喬帶著我們三人來到青龍區一條安靜的街道,指著一棟相對低調的宅子笑道:「這便是薛府瞭。說來好笑,雖然我們祖宅在越城,但傢父和傢祖都因為入京做官,我又自幼便留在昆侖山上拜師,所以過去幾十年荒廢瞭越城的祖宅,京城的別府反而更像傢瞭。」
她拿起暗金色的門環敲瞭幾下後,沉重的木門後傳來一道男聲:「來者何人?」
薛槿喬語調輕松地說道:「是我,槿喬。」
「哎呀!小姐,您回來瞭,小的這就開門!」
一個穿著灰色短褂的中年男子打開瞭大門,見到薛槿喬後面露喜色,深深地行瞭一禮:「前些時日小姐派人來送信後,老爺便一直在掛念著行程。他正在書房呢,還請小姐安頓好後,去見老爺一面。」
「那是自然。崇山,這是我的好友與同僚韓良,與梁清漓、喬三妹兩位姑娘。這三人是我薛府的貴客,告訴章伯,一切按照最高規格招待。我們在京城事瞭之前,他們會在府上歇息。大傢,我得先去見我的爹爹,你們跟著崇山和章伯進去吧。」
崇山對我們施瞭一禮道:「崇山見過韓公子,梁小姐,喬小姐。請與在下一起來,章管事外出辦事,在下會為諸位準備好房間的。」
他帶著我們走進屋子,一邊為我們介紹薛府,一邊詢問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的東西。庭院裡相當空曠,唯有一池潭水,一株樹葉繁茂的梧桐樹,與腳下的鵝卵石鋪就的小徑,並沒有我經常在貴人府邸裡見到的竹林,假山之類的裝飾。
我跟在崇山背後與他閑聊:「槿喬會經常來京城居住嗎?」
「小姐每年都會上京與老爺和夫人過年,不過去年青蓮案發,甚是繁忙,一直到如今才有機會回傢,府上所有人都很是想念她。」
譚箐好奇地問道:「薛傢不是越城人麼?怎麼全傢都在京城?」
崇山回首笑道:「老爺入京在天子身邊做官,繼承瞭薛老爺子的威望,正是咱們薛傢下人的期望,更是嫡系與庶系共同的期盼,自然不在意遷移到京城來。不過,小姐確實一直更喜歡在越城……可惜如今陷於賊手,唉。」
我與梁清漓自然分到同一間房,譚箐的房間則在我們旁邊。崇山微微躬身道:「諸位若是想出府遊玩的話,在下可以叫喚仆從隨行。」
「怎麼樣?要不要個向導?」我對梁清漓和譚箐問道。
梁清漓對崇山道:「那便勞煩先生瞭。」
崇山含笑道:「不麻煩不麻煩,千萬別叫我先生,我這就叫小蘇過來。」
半個小時後,我們出現在朱雀區「永和樓」二樓的酒桌旁。這棟酒樓足有三層高,外面立著一面赤色的酒旗,上面寫著一個大大的「和」字。一樓的廳堂開闊,點綴著花木,墻上的窗戶設著翠綠色的簾子,又通風又美觀,十分雅致。
由於薛傢嫡系隻有薛槿喬這麼一個金枝玉葉的大小姐,府內嚴重地陰盛陽衰,除瞭傢主薛慎之外,就隻有崇山,章管事少數幾個男人,其餘的都是女性。小蘇名叫蘇真,是個十七八歲左右的少女,唇紅齒白,相貌清秀。她與數個年齡相似的少女都在薛府做事,是仆從,也是專門給薛槿喬作伴的閨中侍女。
我觀她帶著我們橫穿街巷,交談點菜時談吐清晰,辦事伶俐,並不像是目不識丁的尋常侍女,便在店小二退下後問道:「小蘇,你看起來像是個讀過書的人,在府裡薛槿喬常年不在傢,都需要做些什麼呢?」
蘇真淺笑道:「奴傢在薛府長大,因老爺對經學修養極為重視,如奴傢這般貼身服侍的仆從也與小姐一同被私塾先生教導過讀書寫字。在小姐離傢拜師之後,便服侍夫人與老太太。」
譚箐饒有興趣地說道:「薛侍郎聽起來像是個很傳統的文官啊,怎麼會讓薛槿喬去拜師學武呢?」
蘇真遲疑瞭片刻後,輕聲道:「奴傢不敢揣摩老爺的心思,但小姐自幼便喜好拳腳功夫,十分活潑,並且天賦過人,因此早早地便有昆侖派長輩前來定下名分。」
我解釋道:「昆侖派擇徒極嚴,需要出身清白,資質優越的年輕人。什麼樣的人出身清白呢?那肯定是受到官府承認的官宦之傢或者勛爵之後最『清白』。而且大部分資質優秀的苗子都是在傢境和出身優越的地方出現的,所以昆侖大多都是如薛槿喬這般權臣或者貴族子弟。昆侖也因此有一個『武林貴族』的名聲。」
閑聊瞭一陣後,蘇真點的菜送上來瞭,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火熏肉,鮮蒸鱸魚,與荷包飯。尤其是荷葉揭開的那一瞬,香噴噴的糯米與肉餡混合在一起產生的濃鬱香氣讓我有幾分見到瞭現代的糯米雞的既視感。
蘇真本人則是對河鮮最上心:「雁嘴江如此近,讓京城的酒樓每日都能吃到新鮮的魚蝦。不過,最好吃的還是江上畫舫直接從漁船購得的河鮮,韓公子若有機會,可以與夫人和喬姑娘一起去嘗嘗。」
我們吃得不亦樂乎時,一個清矍的中年男子帶著一個小廝走上樓梯來,對這一樓的食客行禮道:「諸位好,今日雲裳不在,沒人撫琴助興,酒傢特意請我來為大傢講一講江湖軼事。」
「哎喲,今天陳老叔親臨,好事!」數個似乎認識他的客人見到這個中年人上來,均是歡迎地起哄瞭。
蘇真露出瞭欣喜的笑容,悄聲道:「今天運氣真好!這是陳老叔與他的小童,他是朱雀區最好的說書先生,走遍瞭天南地北,見多識廣,江湖武林的新聞舊事,無不知曉!」
陳老叔取出一塊木板敲瞭敲,開口道:「今日不談別的,就談那青州戰事,田將軍與麾下數萬猛士終於起營攻打濮陽,要從那賊軍手下奪回濮陽,將他們殺出青州去。」
梁清漓訝然問道:「小蘇,濮陽的戰事這麼快便傳回京城瞭麼?」
「奴傢也不知呢,不過陳叔人脈深厚,消息肯定十分靈通。」
我們仔細聽瞭一陣後,發現這說書先生雖然口才瞭得,將青州戰線的故事描述得惟肖惟妙,但並沒有談真正的軍陣對峙或者攻守之勢,而是註重在講述諸多高手的交戰,讓我們這些曉得內情的人覺得十分好笑。真正的高手對決在我們離開之前隻有過一場,那就是我與秦喜合擊右護法的那一戰,而燕京除瞭少數幾人之外,絕不會再有其他知道詳細情況的人。
不過也是,如果他真的消息靈通,得知瞭戰況的話,添油加醋地在廣庭大眾之下亂說一通,恐怕在戰時這種敏感時期,要被衙門捕快找上門來請喝茶瞭,還不如編些大傢都喜聞樂見的高手對打。
啪!陳老叔敲瞭敲手中的木板,神色凝重地說道:「話說那妖教右護法縱橫天下二十年,近些時日更是對上鳳閣行者不落下風,武功之強令人吃驚。他麾下有一文一武兩大『尊者』為臂膀,不容小視。那文者為定遠將軍何定遠,身份神秘,有人猜測是邪道中人,為瞭亂我大燕王氣而來。武者乃有名的寧府內卿,『鐵臂金剛』陶宗敬,一套大力金剛神拳使得出神入化,乃是堂堂的一流高手。」
梁清漓小聲地對我問道:「夫君,你見過何定遠,但『鐵臂金剛』似乎沒人遇到過呢。」
這句話讓蘇真的大眼睛亮起,湊近瞭些聽著我們聊話。我說道:「陶總敬據我所知是個完完全全的武師,除瞭戰場廝殺之外沒有別的能耐,不比何定遠文武雙全,運籌帷幄。濮陽陷落後,軍部還未出擊,他估計貓在城裡練功喝酒去瞭。」
陳老叔煞有其事地介紹完寧王軍方的高手後,眉飛色舞地說道:「不過咱們大燕的青州軍實力隻會更雄厚,且不說輔國大將軍親率大軍,便是麾下的將領與高手便如雲。京城出身的『三丈寒星』趙毅將軍,還有青州馬步軍都總管,曹武略大人,都在營中。當然,武林方的高手也不容小覷,五臺寺的『悲苦頭陀』宗勤大師還有炙手可熱的昆侖派大師姐,『碧華手』薛槿喬,也在濮陽外。去年便是碧華手率領順安精兵攻下瞭太屋山下的青蓮教老巢,不知這次她能否再現神奇,幫軍部拿下濮陽。」
嗯?我倒是沒有想到薛槿喬一個區區二流高手都會被陳老叔提起,不過也是,這可是堂堂的武林白道年輕輩第一人,也是在青蓮案中大出風頭的冉冉新星。畢竟是在講故事嘛,成名已久的高手要有的,而風頭正盛的年輕人也是必不可缺的元素。
蘇真抑制不住好奇地問道:「韓公子,小姐今下提前回京,必是有什麼重大的原因,奴傢不該多問,但她在青州這麼多月,可過得好嗎?」
我與梁清漓、譚箐對視瞭一眼,笑道:「放心吧,她可好瞭,而且還做下瞭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呢。很快你就會知道瞭。」
少女瞪大瞭眼睛,心癢難耐,但十分有定力地沒有追問,而是對我表示感謝後,重新將註意力放在說到精彩之處的陳老叔身上。
等到他說起趙毅與宗勤合力對戰何定遠與陶總敬,一招一式打得天崩地裂,連戰三百回合時,我發現有些不對,感情青州戰事隻是個借用的背景,其中的內容直接就自由發揮,開始連載玄幻小說瞭是吧?
最後,當他說到右護法親自下陣,與田煒定下「三拳之約」,輸者必須退避三日,不得攻擊時,有人忍不住開腔瞭。
「陳老,俺一個師兄聽從軍部招募去青州打仗瞭,他的書信裡可沒有這麼激烈的戰事,你這是從哪裡聽來的?再說瞭,田老將軍哪會親自跟右護法賭鬥?」
陳老叔冷哼一聲道:「你那師兄撐死也不過是個三流之輩,哪能見到真正大人物之間的打鬥?再說瞭,老夫這是在說書,不是在念戰報。」
那倒是,你就說精彩不精彩吧。我看周圍的食客雖然有不少露出瞭不以為然的神色,但都被陳老叔跌宕起伏的故事與技巧純熟的敘述吸引瞭註意力。
「那右護法不愧是叛軍中千軍萬馬的大將,將妖教的鎮教絕學,蓮華大手印,使將出來!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吐八個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使出一招雄渾大力的萬佛歸宗來!這一招石破天驚,堪比羅漢降世,佛祖降魔,但田將軍三十年軍旅浮沉,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他雙手抱圓,紮瞭個馬步,虎目圓瞪,口綻驚雷,喝道:吃我一招旭日大磨盤!一流高手之間的交鋒,威力大得不可思議,方圓百丈內,所有人都感覺到一股氣浪炸開,將上百訓練有素的戰馬都嚇得險些脫韁!」
聽到這裡我們這一桌人都忍不住笑瞭。蘇真聽得津津有味,看到我們的反應,疑惑地問道:「韓公子,陳叔說得有什麼不對嗎?」
我小聲道:「陳老叔對右護法和田將軍的武功不甚瞭解。什麼萬佛歸宗,蓮華大手印沒有這種招數,都是以手印起名,比如千葉蓮印,華蓋印,蓮臺印這種名字。田將軍的武功更是搞笑瞭,據我所知,他的拿手武功是軍中秘傳的『斷山海』刀法,決然沒有空手與右護法這種拳法大傢對戰的理由。」
梁清漓也含笑說道:「小蘇,咱們離開濮陽時,敵軍都還沒排出人馬出城來呢。何況,他們是守城的那一方,面對狀態完好,雄赳赳的官兵,怎麼可能會主動出來求戰?陳老的故事雖然說得好聽,但萬萬不可當真瞭。」
蘇真聽我們的講解比聽說書先生的故事還沉醉,等到陳老叔講完之後,才反應過來,帶著我掏出的一小串銅板賞給他,然後快步跑回桌子來。
小姑娘托腮問道:「可惜陳叔沒有說到小姐的事跡呢,就算不是真的,奴傢也想聽聽。」
譚箐拍瞭拍我的肩膀道:「機密的事項不能亂說,但是自傢小姐的武功和能耐總能吹一吹吧?」
「這倒沒什麼需要忌諱的,見識豐富的江湖人士都知道……朋友,聽得夠久瞭吧?要不要來坐坐?」我突然看向右手側一桌離我們大概十五步外獨坐的男子說道。
聽到我的話,其餘的人也順著我的視線看瞭過去。此時二樓許多食客已經離開瞭,隻剩下我們與一個獨酌的男子在靠窗的這一邊。他三十歲上下的樣子,國字臉,濃眉朗眸,臉色有些蒼白,一身玄色勁裝,腰間別瞭把長刀,是個活脫脫的江湖俠客。
那人也不客氣,徑直起身過來坐在我對面,和氣地笑道:「不好意思,在下不是有意窺探,隻是聽這位仁兄的評價聽得入神瞭。在下冒昧地問一句,兄臺似乎對青州的戰事十分熟悉?」
我挑眉說道:「算是有幾分瞭解吧。在下韓良,這幾位是我的妻子與同行的友人。請問你是?」
他若有所思地說道:「韓良……在下似乎聽過兄臺的名字。這位姑娘亦是有些眼熟,請問姑娘是否薛府的侍女?」
小蘇有些不自然地答道:「是的……」
我起瞭疑心,瞇眼問道:「在下無名小卒一個,不知兄臺是從哪裡聽得我的名字的?」
他露齒笑道:「抱歉,是我唐突瞭。我是名玄蛟衛,姓田,名道之。」
田道之?
當年京城派去順安支援我們的玄蛟校?我記得寧王起兵時,他帶著人馬在懷化行動,失去瞭聯絡,這大半年來我都沒再收到他的消息,他還活著?
看到我難以置信的臉色,田道之說道:「韓兄似乎也聽說過在下的名字,我便不兜圈子瞭。同為玄蛟衛的秦喜與唐禹仁,都是我的同僚與朋友。唐禹仁更是與我關系甚近。我也是從他們,也從碧華手口中,聽到關於韓兄的事跡的。」
「田道之的名字我確實聽說過,但你不是在懷化行動嗎?又是如何輾轉到京城來瞭?」
田道之似乎被這個問題勾起什麼不快的往事,皺瞭皺眉答道:「原來韓兄也聽說過此事……在懷化那段日子確實是段驚險的經歷。寧王反叛後,我並沒有第一時間離開懷化,而是在城內潛伏瞭數個月後,才帶著足夠的情報脫身。而今我上京來,正是為瞭求見統領。我喜歡在酒樓,茶館歇腳聽聽江湖傳聞,搜集信息,卻是不意中撞上瞭諸位。」
原來如此,這倒是個不大不小的巧合。
「聽說薛小姐和我的兩位同僚都在青州為軍部做事,怎麼也來京城瞭?」
我含含糊糊地說道:「發生瞭些事,薛槿喬覺得有些東西要回京稟報。抱歉,這件事眼下還是個軍部機密,我無法告知。」
田道之理解地點瞭點頭,笑道:「明白,我們這一行需要保密的東西可多瞭。秦喜和禹仁可好?」
我嘆瞭口氣道:「禹仁跟我一起上京來瞭,秦喜留在青州……他受瞭重傷,必須靜養。你若要求見統領的話,應該會碰到禹仁,他可以跟你敘敘舊。」
田道之怔瞭怔,仔細觀察瞭幾眼我的臉色,理解地說道:「是這樣麼,那可惜瞭,我還想與他們一起喝杯酒呢,希望秦兄能早日痊愈。韓兄與夫人若是準備在京城多留幾日,希望能叫上禹仁與你們再見一面,好好聊聊兄臺在青州的見聞。在順安咱們一直有緣無分,此時相逢,正是天意如此。」
「好說好說。」
田道之起身抱拳行瞭一禮後,拋下幾塊碎銀悠然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