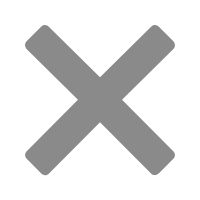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二章 玩笑
敏是我的初戀,如果單純用性關系發生與否來劃定戀愛界限的話。她是我的第一個女人,對於一個十八歲的小夥子來說也許過於早瞭些,透過她我得以窺見生命欲望的秘密,我就像飛蛾看見炫目的燈火那樣,不顧一切展翅義無返顧地撲瞭進去。我的下體猶如一把鑰匙,插進她的鎖道,把潘多拉的魔盒打開瞭,我的生命中的某扇新鮮的大門從此被開啓,我進入瞭全新的未知的世界。
我認識她完全是一個無厘頭式的偶然,不像現在追求一個女孩子那樣大費周章,又是送花又是請吃飯,經歷瞭不停地試探,迂回曲折才能成功。一切就因爲我對陌生人開瞭一句陌生的玩笑。
我後來慢慢地回想起所有的這一切,都不知道自己當時爲什麼要說那些話,爲什麼要那樣說,爲什麼要那樣做,仿佛生命中某時某刻遇見某個人是註定的,生命的臺詞和情節早已設定好瞭。這也是我現在深信某些看似並不可信的神秘的事物的根源之一。在一個薄霧冥冥的星期天的清晨,東方將曙,秋季的天空變得格外的高遠幹凈,東方泛著讓人振奮的魚肚白的顔色。
我買瞭蔥油餅埋頭一路走一路吃,拐進瞭回小屋的巷子,全然沒有註意到前面走著一個身材姣好的女孩。我一擡頭就看見瞭前方的她,離我不過四五步遠,一頭齊肩的黑發,飄逸而柔軟,隨著她輕盈的腳步在秋天晴朗的晨風裡飛舞,纖腰盈握,臀部渾圓挺翹,雙腿豐腴秀長——這是一個已經發育成熟的女孩子。
她一直頻頻地回頭,但是沒有看見我,她轉頭是低頭看她自己的屁股,我很好奇,忍不住說瞭句:「嗨,屁股上有朵花呀?」。她不是我熟識的朋友,即便是很熟悉的朋友我也不會開這樣的玩笑,我也不是一個輕浮的善於言辭的人,自小到大我都是一個積極向上一本正經的孩子,多年以後我想起這句開場白的時候,仍然驚訝不已,我爲什麼知道她不會嗔怒於陌生的男孩輕佻的話語?隻有一個唯一的解釋,如我所說,這是生命中被設定的臺詞之一,信手拈來,隨口而出,沒有來由。
她像隻受瞭驚的兔子,擡起秀麗的面龐,飛快地看瞭我一眼,面頰緋紅。
她怔怔地笑瞭,突然很驚訝地說:「呀,我認識你,你是老中學高三的的第一名,叫向……」,她一時想不起我的名字來。
我有點受寵若驚,有點不好意思地低著頭,這也許是我常有的習慣,也可能是所有人年少時常見的通病。我知道我是第一名,我還知道當地有些人把我們那座小屋叫做「狀元樓」,這是相當誇張的,但是我很少聽到從別人的嘴裡說出來,而且是從如此美麗的女孩的嘴裡說出來的,我想我當時的臉上呈現瞭青澀的得意的羞怯。
我沒有去問她是怎麼知道我的,那樣顯得太不低調瞭,,不是我慣有的風格。我接著她的話說:「向非,什麼第一名哦,我隻是運氣比較好點而已。」這是爸爸面對別人對我的贊揚時常說的一句話,爸爸是最瞭解我的人,他說的也許是實話,不過我覺得這句話挺好的,就記住瞭,卻不知在這時排上瞭用場。
她咯咯地笑瞭,說:「我還以爲第一名是個書呆子,愣頭愣腦的模樣,瘦弱的身體,沒想到是這麼個英俊的帥哥哩。」這句話讓我臉有點燙,我並不自戀,但是很多人都這樣說過,有時候連媽媽也會這樣說。
她說她要去菜地裡摘菜,剛好我們順路,我們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往前走,從交談中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敏,新中學高三的,同級生讓我們彼此的距離拉進瞭好多,不再像剛開始那樣尷尬瞭。從小到大,不管男生女生,我都從來沒有發現一個如她這般親近可人的,像是見瞭故人一般親近。
她的聲音很好聽,說話時露出潔白細密的牙齒,笑起來的時候大眼睛向上彎成一線,長廠的睫毛也跟著微妙地律動,雙眼皮。她那天穿著白色棉質的長褲,上身也是白色小坎肩,裡面穿一件淡青色的線衫。臉蛋兒沒有化妝,光潤潔白得沒有一點瑕疵,鵝蛋臉,下巴圓潤,眼睛很大很有神,笑起來細細的眉毛生動地玩起來,很是迷人,我多想和她一直說著話,可是我到瞭住處瞭,我要走到院子裡去的時候不得不跟他跟她道別。
她說:「你就住這裡啊?我傢菜地就在前面不遠,房東我也知道,他是我表姥爺哩。」
我說:「你表姥爺就我一個房客,有時間你可以來找我玩呀,我很多時間都在。」
她歡快地笑瞭,問我:「我可以帶著作業來問你數學題嗎?我的數學好差的,老是考不及格。」
今天我也說不出的開心,我也笑瞭:「當然可以瞭,你來瞭你就在院子裡面叫我,我聽得到。」
因爲閣樓上有個木格小窗,從那裡可以看到院子裡面。她點瞭點頭,像隻小鳥那樣跑開瞭,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穿過滴著露珠的樹葉,追逐著她輕盈的腳步轉過彎不見瞭。看著她在我眼前消失,我不知爲什麼莫名其妙地有點悵然。
我拿著沒吃完的油蔥餅,爬上院子的土墻,坐在墻上享受著秋日裡暖暖的陽光,這是我星期天早上常有的習慣。但是今天不太一樣,我的心裡滿是期待,我的目光遠遠地瞅著她消失的路口,期待著我的小鳥再次出現。
陽光灑滿院子的時候,敏終於出現瞭。她遠遠地向我揮手,我也站到土墻上向她揮手。她走到跟前,擡起頭看著墻上的我,額頭上滿是細密的汗珠,在陽光下細微地閃著光。
她說:「你有空嗎?我吃完早飯過來找你。」
我說:「你快點來,我在這裡等你。」
我搬到這裡來之後,除瞭上課下課,偶爾有從傢鄉一起過來小夥伴過來陪我玩之外,時常一個人,我有點著急,太需要朋友瞭。
我在土墻上等瞭很久,她還沒有來,我耷拉著有點疲憊的腦袋,看看天空又看看河道,太陽慢慢地移向澄凈瓦藍的天中央,遠處的河道裡升起蜿蜒輕盈的白霧又散開去,由濃密而稀薄,越來越淡。我終於等不住瞭,秋日的太陽把我的頭曬得昏昏的,像喝醉瞭酒,我從土墻上跳到院子裡,摔瞭一屁股,爬起來揉著屁股走到閣樓上,倒在床上睡覺去瞭。
正睡得香的時候,迷迷糊糊中聽見有人在輕輕地叫我的名字,那聲音甜甜的,輕柔得像陣風,我還以爲是在夢裡。我睜開眼,屋外的梨樹上秋蟬在不知疲倦地聒噪,鳴唱著夏日的挽歌。我從窗口循聲看出去,正看到她抱著一疊書站在庭院的老梨樹下,微風撩起她的發絲,拂過她娟秀的臉龐。
由於初睡乍醒,我感到頭有點痛,踉踉蹌蹌走下樓去給她開門。她走上樓來,屋子裡彌漫著淡淡的香味,仿佛梔子花的味道。她把書放在我寫作業的方桌上,四下打量著我的小窩,嘆氣地說:「好好的一個地方,怎麼不懂得收拾一下呢?」
我窘迫地笑瞭,我覺得已經很幹凈瞭。說完她就像個老朋友一樣幫我整理起房間來,又是整理書本,又是整理床鋪,就像是在她傢裡一樣。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有點猝不及防,一臉窘然地站在一邊,不知道做什麼說什麼才好。
她回頭看瞭看我,笑瞭:「愣著幹什麼呢,去把掃帚和垃圾籮拿上來!」仿佛我是她的仆人一般命令我,可是我莫名其妙地很開心,飛快地完成瞭她交代的任務,還主動地打起下手來,仿佛她才是小窩的主人,而我隻是來訪的客人一樣。
我搬進來的時候這個閣樓已經廢棄瞭好久,也沒怎麼打掃幹凈,我們花瞭好長的時間才完成打掃,而我們也已經忙得滿頭大汗瞭,她的秀發都弄亂瞭,交錯縱橫地貼在額頭上。閣樓變得煥然一新,書本整整齊齊的放在方桌上,被子也整整齊齊的,洗過的地板散發著櫸木腐爛老朽的香味,混雜著飄在空去中的微塵的味道,閣樓也變得格外地寬敞瞭,變得格外地亮堂瞭。我突然發現我還是喜歡幹凈的,如果和之前相比較的話。
我和她走到院子裡面去洗臉洗手,也好讓閣樓自個兒清靜一下,到瞭院子裡才知道已經日薄西山瞭。我突然想起她是來讓我輔導她做作業的,我就問她:「我們休息會兒去做作業吧?」
她伸著懶腰說:「都忙活得累瞭,滿身塵土,要不我們去河裡洗澡吧?」
我還不知道這裡除瞭澡堂在哪裡洗澡呢,她跟我說河邊有溫泉,天然的溫泉不用收費的。我們帶上香皂盒浴巾,朝河邊的溫泉走去。
太陽已經西下,掀起瞭漫天的晚霞,我們就在金碧輝煌的霞光裡走著笑著。經過昨晚偷窺小寡婦的香艷,我已經初知人事,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和敏在一起完全沒有瞭那種邪念,她約我的時候就像小夥伴約我上山放牛那樣自然,我隻想和她在一起時間長點,隻想看著她說話,看著她的眉眼,看著她的笑。
其實河邊也不遠,大約也就二十分鍾時間。到瞭河邊,遠遠看見河岸兩邊升起一團團白白的暖霧。河邊的溫泉很多,零零星星地散佈在河岸兩邊,我們那裡也有的。已經有人洗澡瞭,傳來男男女女的嬉鬧聲。
我們找瞭個僻靜的地方,她讓我赤腳走到河水裡,打開河水的一個缺口,讓河水灌進來,調好水溫,我開始脫衣服,回頭一瞥,她蹲在河邊的石頭上沒有動靜,我叫她快點,她咯咯地笑瞭:「你倒想得美,我不和你一塊洗,你先洗好瞭,我再洗。」
我才突然意識到,我們不是哥們兒,她和我不一樣,她是個女孩。想到這裡,臉一陣陣發燙,提著褲子不敢往下脫瞭。
她看著我的窘樣,哈哈大笑起來:「大男生還怕吃虧瞭?」
我還是沒這個勇氣,我做瞭個鬼臉:「你轉過身去,我下水瞭你再轉過來。」
她哼瞭一聲:「我蒙著臉還不行嗎?」說完把雙手捂住眼。
我飛快地脫下褲子和內褲,跳進水裡她才把手拿開來。我一邊洗一邊和她聊天,她說她是傢裡最小的孩子,而我卻是傢裡的長子,她說她學習很認真,就是成績不好,我說我從小到現在一直是第一名,她瞪大瞭眼不敢相信,問我可不可以幫她補課,我求之不得呢,那樣放學後我就不用一個人孤單瞭,我也想和她待在一起。我說我其實我並不是很聰明的人,我隻是勤奮而已,起得早睡得晚,作業做完才休息。
我沖洗幹凈身上的香皂準備出來瞭,我叫她轉過身去,她很聽話地轉過身去瞭。我正在浴塘邊用毛巾擦幹身子的時候,她突然轉過身來,大叫一聲:「穿好瞭沒有?」嚇得我轉身又跳進瞭浴塘,她哈哈開心地笑瞭,前仰後合,笑得眼淚都出來瞭。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她才轉過身去讓我穿好衣服。
這回輪到她下去洗瞭,我跑到她的位置,打算在她脫衣服的時候蒙著眼或者轉過身去,可是她不幹,非要我往前一直走,走到她滿意的距離才讓我停下來。
這時已經薄暮冥冥瞭,東方天際的那顆啓明星開始若隱若現,蠢蠢欲動地要掛上天幕。我回頭朝她那個方向望去,暮色中隻看見一團白花花的影子在動,倏忽就不見瞭。我知道她進瞭浴塘瞭,大聲地問她:「我可以過來瞭嗎?」
她尖叫道:「不可以,你過來幹嘛?」
我沒理會她,徑直走過去,誰叫她剛才她還嚇唬過我呢。她一直尖叫著:「不要過來,不要過來……」,聲音帶點哭腔。
我走到她跟前,在浴塘邊上直勾勾的俯視著她,她縮著身子雙手抱胸蹲在水裡,濕漉漉的頭發披散在秀美的臉龐上,她小聲地說:「你這樣我怎麼洗啊?」
我笑瞭,我本來就是嚇唬她一下而已,我走到她之前坐過的那個石頭上坐下來,轉過身去,浴塘裡傳來嘩啦嘩啦的水流滑過肌膚的聲音。我很想轉過頭去,剛才她雙手抱胸時,我看見瞭那雪白的被手臂勒得鼓滿出來的鼓脹,讓我想起瞭小寡婦那變形扭曲的東西,心裡砰砰直跳,我還沒有這麼近距離的看過女孩的胴體呢。
可是心裡面有個聲音一直告誡著我,在不停地說服我:千萬不要打開潘多拉的的寶盒,裡面住著魔鬼。我很無聊,漫無邊際地想著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我依稀記得我想起瞭外婆傢那個村子,春天到處開著爛漫的桃花;老傢後面的山裡原野上,到處開滿迷人的小野花……
她柔美的聲音再次響起,把我的思緒從遙遠的地方拉瞭回來——她已經穿戴好瞭,我還打算在她穿衣服的時候突然轉身嚇她呢,誰想到她這麼快就穿好瞭,也有可能是我沉迷於漫無邊際的思考太久瞭,我常常有這種幻想的習慣,到現在還改不瞭。
在回來的路上,她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我看到瞭你那裡瞭。」
我說:「哪裡?」她用手指瞭指我那裡。
我的臉唰地一下燙瞭,爲瞭證明她不是開玩笑,我著急地問她:「什麼樣子?」
她笑瞭:「我怎麼看得清呀,夜色那麼濃,不過看起來挺大的。」
我驚訝地說:「挺大?我也看見你的瞭。」
她搖著頭說:「不可能的,你一直背對著我的。」
我裝得認真起來,說:「我真的看到瞭,好白,那裡的毛少少的。」其實我哪裡看得見嘛,白倒是真的,我在魚塘邊上俯視她的時候看見瞭,在夜色裡她的肌膚微微地泛著誘人的銀光。
她惱瞭,追著我打……現在想起來,年少時那些莫名其妙的對話,其實並沒有什麼邏輯可言,混雜不清,東扯西拉。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動機可言,然而其實上少男少女的欲望的觸角已經慢慢地小心翼翼的悄然試探著對方。
到瞭我住的小屋,我叫她進屋裡去休息會兒。她說不要瞭,太晚瞭,叫我上閣樓上把她帶來的書拿下來。我把她的書拿下來給她。臨別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她明天還會來的,我已經答應瞭給她補課的。
那年月我們還沒有用手機,無法隨時聯系,我能做的隻有焦灼的等待。我清晰地感覺得到內心隱密的騷動,像一隻潛伏的獸在慢慢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