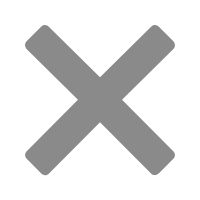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三章 初夜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腦子滿是她的影子,滿是她的一顰一笑。一堂課對我來說好像變得長瞭,老師在講臺上像個無聲的玩偶動來動去,是那麼的可笑和滑稽。好不容易挨到放學,飛快地跑回小屋,在院子裡踱來踱去,滿心歡喜的等待她的出現,事實證明,等待是件惱人的活,時光在傍晚的斜陽裡拉長瞭影子不情願地緩緩移動。
她終於來瞭,我心喜若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狂瞭。可是上瞭閣樓,我的心卻突然安靜下來,我又找到瞭和小時候的夥伴一起放牛的那種親切感。
我們在一起學習,我很認真的給她解答她不懂的地方。時間突然像長瞭翅膀,飛快地流失,很快到瞭晚上,她就回傢去瞭,留下孤零零的我。她走後我開始心慌意亂,我覺得我變得不開心瞭,遇到她之後我仿佛變得更孤獨瞭,仿佛平靜的湖面被投進瞭一粒石子兒,水面蕩漾著不肯平靜。
我們就這樣過瞭一個星期之後,她突然就沒有來瞭,就像憑空蒸發瞭一樣。我像生瞭病一樣躺在閣樓上,懶懶的不想動。我不知道她怎麼瞭,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她,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她在新學校讀高三,至於讀哪個班我都不知道。
在我生不如死的時候,在新學校讀書的表弟來找我玩,我央求他,幫我我去找找她,我給她寫瞭一封信,在信裡說我很想她。就就這樣病懨懨的,整天神不守舍,在焦灼難耐中度日如年,自己就像變瞭一個人一樣。
終於在一個晚上,天剛擦黑,表弟終於把那救命的稻草帶來瞭。她回信瞭,她給我回信瞭,她在信裡說她這幾天生病瞭,說她也很想我……
她還在信裡說在街口的麻將館旁邊等我。我獲得瞭拯救,重新精神煥發瞭。
我在麻將館的旁邊找到瞭她,她好像真的瘦瞭一些。
她已經買好瞭很多東西,她問我:「我們去哪裡呢?」
我有點不知所措地說:「我不知道。」我沒約過會,這是頭一次,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約會是需要地方的。
她笑瞭,說:「我知道個地方,我們去那裡吧。」
我就跟在她後面走,那天天空很晴朗,漫天的星星,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快走幾步上前抓住她的手,緊緊的抓住,她甩瞭幾下,就停住瞭,任由我握著。
我們來到郊外的一片苜蓿田裡,遠離瞭小鎮的喧鬧,在這裡我吻瞭她。從此我們就是戀人瞭,我有瞭第一個女朋友。
誰不記得第一次約會的情景呢?很多事情是在回憶裡變得妙不可言的,當時的人不自覺而已。
我們相約來到田野裡,大片大片的茂盛的苜蓿,我們就仰天躺在上面,像躺在厚厚的床上,看頭頂上鑲著漫天的星星的蒼穹,銀河都看得分明,依稀能聽見銀河流轉的聲音。對面是萬傢燈火,這裡一片,那裡一片,這些聚落讓人倍感溫馨。我們帶瞭東西去吃,有油炸的蠶豆,有瓜子,像兩隻田鼠唧唧喳喳地吃著東西,說著話。
我們沒天沒地說瞭好多話,東西吃完瞭,就沒說的瞭。她不說話瞭,我也沉默下來,周圍萬籟俱寂,秋蟲的吟哦聲此起彼伏。她閉著眼睛,好像睡著瞭,又好像不是。
我百無聊賴地搖瞭搖她,我問她:「我們是不是該回去瞭?」她不動也不言語。
我又說:「你不說話我就不老實啦?」她還是不說話。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說「不老實」,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應對這樣的場面,我隻是從他們的口中得到一些混雜的資訊,才有瞭模模糊糊的一點意識。我的一個小夥伴是個花心大少,他約會回來總是會炫耀他的約會經歷,對如一張白紙的我來說,裡面都是些新鮮的體驗,我常常表現得不以為然,但是我心裡記住瞭他的那些行為,現在正是派上瞭用場。
我也不知道知道她是不是默許瞭,就壞瞭一下,親瞭她的鼻子一下,感覺鼻尖有點冰。她沒有拒絕,我抬起她的下巴,吻她的嘴唇,薄薄的還是冰,像兩片玫瑰花在水裡泡過一樣,可能是季節的關系,時值十月初瞭。
我貼住她的嘴唇,急切地把舌尖探進她的唇縫裡,她卻吝嗇地咬緊的牙齒,我的舌尖在她的齒間舔吸奔突,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她慢慢地松開瞭牙關,露出一丁點舌尖,隻能觸接到溫軟的肉尖,卻無法咂吮,這使我情急起來。我緊緊地吻著她,不願放開,她的嘴唇漸漸翕開,芳香的氣息流轉而出,微微弱弱。
她把舌頭吐出來的時候,嚇瞭我一跳,像條小蛇鉆進嘴裡,溫暖而濕潤。我很怕但是很渴望,溫軟的濕潤的,有點香,有點甜。很多年後,我在書上看到一個詞兒——丁香暗吐,我想就是這樣的感覺吧。我想就這樣含著吸著,到地老天荒。
從東邊的山頂上爬出來一輪圓圓的月亮,十月初的南方夜晚,不溫不熱,是最清新乾凈最美好的時刻。天空又高又遠,沒有一絲雲霧,像是被清水洗過藍瑩瑩的。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傾瀉下來,瀉在河的兩岸,瀉在飄著稻香的梯田裡,瀉在我們身上。不知名的蟲子在田野裡撒歡地叫著,遠處的枝頭也有睡不著的小鳥喧鬧聲。
我們一邊吻著,我一邊把手從她上衣的下擺摸索進去,探進她的乳罩裡面,溫熱的體溫,柔軟豐滿的乳房,在我的掌中扭曲變形,她發出瞭難受的喘息的聲音。我感覺得到那兩個肉球慢慢地漲大,變得很有彈性。
我騰出一隻手,另一隻手繼續揉捏她胸前的鼓脹。我探倒她腰上皮帶的齒扣,飛快地她的皮帶解開,抽出來甩在一邊,她卻把我的手給抓住瞭,她驚惶地睜開眼,抬起頭來,狠狠地看著我,說:「看不出來啊,原來你這麼壞啊,這些都是跟誰學的?」
突兀裡來這麼一問,我的動作便停瞭下來。我抬頭看著她,我從她的眼裡看出在夜色裡的驚懼,我想我當時像頭野獸,好像有一個妖怪在身體裡潛伏瞭十八年,突然露出猙獰可怕的面孔,目光是銳利而兇悍的,所以嚇壞瞭她。
我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怎麼變得那麼奇怪,顫抖中夾雜著哀求,仿佛不是從我嘴裡說出來似的:「我……聽……他們……說的……」
她說:「騙子,我看你就是個壞人。」
我都著急得快哭瞭,說:「我沒有,我沒有。」我腦海裡滿是小寡婦的那個白花花香馥馥的肉饅頭,便把手頑強地往下伸展,她死死地把我的手攥住,不讓我移動分毫,我便不能前進分毫。
我急切地說:「你給我摸摸!」
她喘著氣說:「不,你告訴我你的第一個女孩是誰?」
我說:「我沒有,真的。」她抬起頭來用狐疑的目光盯著我,我害怕和她的目光對視,就把頭低著。
良久,忽然她冷冰冰地說:「喂!你知道你在於什麼嗎?」
我說當然知道。「啪」的一聲響,她給我一個大耳光,好似一聲耳邊驚雷,震得我的腦袋嗡嗡地響。
我便惱怒起來,把她按住,好像抓住瞭一個要逃跑的竊賊,壓瞭上去。她反抗瞭,她簡直著瞭魔似地在抵抗,像條垂死掙紮的蛇。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我的手頑強地向她褲襠裡面伸進去,被她的手攥得生疼。這樣的對抗持續瞭很久,弄得我們氣喘籲籲,我額頭上冒出瞭汗珠。
為什麼要這樣抵抗?我自己也不知道。總之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很清楚這事情開弓就沒有回頭箭,要麼成要麼敗,我的小夥伴就這樣說的。
突然她的手松開瞭,輕輕地喘著,嘆口氣說:「我不知道你這麼壞,我太相信你瞭。」
我說:「是你讓我我這麼壞的,我控制不住自己。」
她說:「你再這樣我叫救命瞭?」
我壞壞地笑瞭:「沒人聽見的。」這裡已經是郊外瞭,離我的住處還有好一段距離。
她果真叫瞭起來:「救命啊……」嬌嫩的呼喊在田野裡夜空中遠遠地傳開去,我急忙捂住她的嘴。
她把頭甩開,咯咯地笑起來:「原來你也害怕呀?」
她的笑鼓勵瞭我,我輕輕地把她的手按住,好像按住一隻蝴蝶;她不再掙紮,隻是問:「你愛我嗎?」
我說:「愛。」
她問:「永遠?」
我說:「嗯。」
她說:「你想要我?」
我說:「嗯。」
她說:「永遠?」
我說:「嗯。」
她說:「你是第一次?」
我說:「嗯。」
她啼笑道:「傻瓜。」
我說:「嗯。」我真的是童男子。
她問:「你那裡什麼感覺?」
我說:「它想出來,憋得不舒服。你呢?」
她說:「癢,熱得難受。」
我說:「怎麼辦?」她沒說。
她抓著我的手放在她的小腹上,那裡的肉光滑得像玉石一樣。我的手指沿著滑瞭下去,經過那裡的時候,感覺太奇怪,稀稀疏疏的草地一樣,很短的茸茸的,那裡的肉高高隆起,把我的指尖弄得寂寞難耐。
她把身子挺瞭一下,我的手又向下滑瞭一下,到女孩子那個神秘的去處,好濕潤。我心裡害怕極瞭,指尖順著那個縫陷進去,趕忙縮回來。想再進去,她就用手抓住瞭。但是我深深記住瞭,那裡和我們不一樣,有點軟踏踏地,是個魔鬼的沼澤。
她說:「輕點,我還是第一次。」
我說:「嗯……」
她說:「你先脫。」
我問:「我脫?」
她說:「嗯,你先脫,不願意?」
我說:「哪裡?」
我直起身跪著,把皮帶解開,連內褲一起褪在大腿上。我那兒裸著,硬硬地,長長地豎著,使得我覺得有點怪怪的,很不好意思。她支起上身,目不轉睛地盯著我那裡看。她伸出一隻手,用手指輕輕包攏住我那兒。
她說:「好大喔。」
我說:「你喜歡嗎?」
她說:「喜歡。」
她爬過來吻住我的嘴唇,一隻手抱住我的頭吻我,另一隻手,摸我的胸,摸我的那裡,摸我的睪丸,摸我的陰毛。我抱住她的腰,雙手插進她的褲子,抓著她渾圓而新鮮的屁股用力地捏。她嗷嗷地叫著。
我問:「你不脫衣服?」
她說:「你幫我脫。」
我說:「褲子也要脫嗎?」
她說:「傻瓜!」
我把她的外衣扒開,她高高地擎起雙手,我把她的T恤撈起來從頭上脫下來。我把它們攤開放在被我們滾得平展的苜蓿上。
我問她:「乳罩從哪裡解?」
她說:「傻瓜!」
我說:「哪裡?」
她說:「後面。」
我把手從她的腋下繞過去,她把頭搭在我的肩膀上等待著。我找到乳罩結合的鉤扣,卻不得要領,怎麼也弄不開。
她說:「笨。」反手很容易地解開瞭。
她說:「你也把衣服脫瞭墊著,有點涼。」
她側身躺倒衣服上去,然後面朝上躺平瞭。
她說:「來。」
我說:「沒脫褲子呢?」
她說:「來脫呀,不脫怎麼幹?」
我說:「我來脫?」
她說:「嗯。」
我像隻爬行野獸那樣爬到她的身邊,把她的牛仔褲往下扯。她抬起臀部,褲子便同那內褲順著蓮藕般嫩滑的雙腿褪瞭出來,她把雙腿卷曲起來,衣物滑過腳踝脫瞭下來,乜斜瞭眼眸迷離地看著我。
她問:「你不脫?」
我說:「要脫的。」
我便把自己也赤裸瞭,翻身壓上去。月光下兩條白花花像是被擱置在岸邊的魚,那麼饑渴,就快死去瞭,喘著粗氣。我嗅著她的味道,這味道有些膩又有些發甜,類似於熟透的小麥的香、除去瞭粗糙的衣服,眼前全是潤滑的肌膚緊挨著,潤滑和堅實壓迫著,田野裡散發著溫暖的涼意。
她說:「我害臊。」她把臉朝著別處。
我說:「我也害怕。」
她說:「怕什麼?」
我說:「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有害怕。
她說:「我怕疼。你說過會輕的?」
我說:「嗯。」
她說:「萬一你不愛我瞭呢?」
我說:「我愛你。」
她說:「我們以後要結婚?」
我說:「嗯,結婚。」
她說:「生孩子,漂亮的孩子?」
我說:「嗯,漂亮的。」我忍不住笑瞭,那絕對是漂亮的,而且當時我也那樣想瞭。
她問:「要。」
我說:「要什麼?」
她說:「日我那裡。」她用瞭「日」這個字。
我說:「哪裡?」
她說:「屄。」
我便把那鼓脹在她的雙胯間亂戳,我以為很容易就進得去的,她仰著頭捂著嘴緊張的等待著。我借著月光看到瞭她的粉紅的縫,朝著那裡插去,結果還是不行,龜頭沾滿瞭她的亮亮的液體。那鼓脹像是在第一次在密林裡迷路的小孩,驚惶地東奔西突,可憐而無助。
我說:「進不去。」滿頭大汗。
她說:「不對,不是那裡。」
我說:「哪裡?」
她說:「往下一點才是。」
我按照她說的往下戳,她突然大叫起來:「不是那裡!」
她支起身子來,說「我幫你。」
她騰出一隻手來,握住我的棍棒,像牽著一頭牛的牛鼻子上的繩子,拉向她的圈裡去。我的頂端一接觸到裡面的嫩肉,突然活潑起來,突然滑落進去,緊緊地不可抗拒地滑落進去。
她大叫著:「啊……」馬上感情用手捂住瞭嘴,好像那聲音很奇怪,不是她發出來的一樣,使她驚恐。
包皮瞬間被全部批翻瞭,我不知道還能如此批翻到如此程度。溫嫩潮濕的肉四面八方貼緊瞭新露出來的肉,使我癢得難受,我忍不住往裡面突進去。
她說:「痛……」使勁地推著我,不讓我前進。
驟然而不可抑止的征服欲,使我不再受她控制,也不受自己控制,猛烈地日她,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寬廣無極草原縱情馳騁,耳邊風聲烈烈。她哭叫著,扭動著,使勁地用拳頭捶我的背,打我的胸,用嘴咬我的臉,我不知道什麼叫疼痛,我隻知道我很癢,我要日,一直日……向著光輝的頂點直奔。
她退讓瞭,她馴服瞭,不在打捶的背,不在打我的胸,不在咬我的臉。而是抱著我的脖子,按向她的脖頸,她的乳房,我吻著她,舔著她,幹著她……
她裡面有一種新奇的東西,讓人驚心動魄的東西,美妙得無法言喻,把我溶解,把我整個內部溶解瞭。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瞭一個威脅她和壓服她的人,比她更強有力的人。我們一同在潔白的月光中飄升,飄升。
她躺著伸直瞭頭,發著細微而狂野的呻吟,更加歡快地扭動著叫喚著。我突然感覺一陣麻癢,這麻癢像觸電一般,瞬間傳遍我的全身,覺得從每一根頭發到腳尖的指甲都激靈瞭一下,然後又聚集在那頂端,一並爆發開來,如煙花呼嘯著送入藍黑的蒼穹,在最高點轟然炸開,光耀大地,無數的煙花粉末在夜空中寂寥地簌簌下落,泛起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慵懶,我便匍匐在她身上不動瞭。
我結束得太快瞭,太快瞭,讓我羞愧難當;
她問:「射裡面瞭?」
我說:「嗯。」
她又開始打我,捶我的胸膛,咚咚直響。
她說:「要生小孩瞭。」
我說:「嗯。」
她說:「怎麼辦?怎麼辦?」」唔唔地哭起來。
我說:「你說要生的。」
她說:「我媽媽知道要打死我。」
我說:「讓她打我,讓她打死我,我保護你。」
她說:「你不怕痛?」
我說:「不怕,你打我一點都不痛,不信你試試。」
她握起拳頭,對著我的胸口又是一陣亂捶。她終於破涕為笑瞭,又哭又笑。
她爬起來,跪在「床」上,低頭看著她的下面,突然驚叫起來,「血,出血瞭。」
我一下跳起來:「哪裡?」
她指給我看:「那裡。」我看見瞭我的襯衫上巴掌那麼大一團血跡,像一朵被揉過的玫瑰花。
她從衣服的袋子裡找出紙巾,扔給我,自己低頭擦那下面。我也擦瞭,紙巾上也有血。
我問她:「是不是來瞭?」
她說:「不是的,剛剛走。」
我覺得壞瞭,是不是我把她日壞瞭,我讓她給我看看,她說:「不要,笨蛋,都被你弄破瞭,痛。」
我問:「還痛?」
她說:「不痛瞭,剛開始好痛的,後來就不痛瞭。」
我說:「後來就不痛瞭?」
她說:「嗯,後來很舒服,癢死瞭。」
我說:「我一直癢,不痛。」
她說:「我現在還癢。我要你再日我。」
我說:「現在?」
她說:「嗯,來吧,日我。」
我說:「別瞭,都出血瞭,明天我們再日好不好?」想著帶血的幽深的洞穴要再次吞沒我,我不免有些害怕。
她說:「明天哪裡?」
我說:「你來找我,我等你。」
她說:「我喜歡月光,我喜歡這裡,我等月亮出來來這裡幹啊。」
我說:「嗯。」
我們穿上各自的衣服,她讓我把她的乳罩鉤扣扣好,這回我做到瞭。她用手把頭發梳理瞭一下,好讓它不像剛才那麼淩亂。
我問她:「這樣回去會被媽媽罵嗎?」
她說:「不會,我說去燕子傢瞭,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還在她那裡過夜呢。」
我說:「你不去我那裡?」
她說:「明晚吧,今晚不行,我媽媽會問燕子的,明天我跟她說好才行。」
我的襯衫穿不成瞭,我隻好隻穿著外套送她回去。到瞭她傢門口的時候,她一把把我的襯衫奪過去,她邊跑進院子邊笑嘻嘻地說:「洗好瞭還給你!」
這天晚上是我睡得最好的一個晚上,那麼香那麼甜,仿佛閣樓上還有她少女的奇異香味籠罩著我,她的舌還纏繞著我的舌,我的下面還幹著她溫濕的下面,就那樣在夢裡吸吮瞭我一夜,就那樣在夢裡幹瞭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