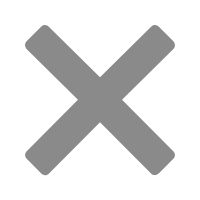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九章 拖拉機和馬車
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蒙蒙亮,微弱的光線穿過屋頂那片透明的玻璃瓦投射進來。我常常想知道黑暗的夜晚和光明的早晨是怎麼樣轉換過渡的,試圖分別它們之間清晰的界限,多少次在黑暗中等待那一刻,卻發現光明的光線如此無聲無息,在不經意間,早已彌漫大地,找不到它來到的那個剎那,仿佛它早就潛伏在黑暗之中,如同黑暗潛伏在光明之中一樣。
外面樹上的小鳥隱隱約約地不安地低鳴,似乎要醒來或者正準備醒來呢。空氣很潮濕,似乎天還是陰著的,隻是雨住瞭。
昨天睡得太久,再也睡不著瞭,我直起身正準備下床……敏「嚶呤」一聲翻瞭個身,從剛才的背對著我側臥變成瞭仰臥,不經意地把一條腿腿搭在我的腿上。
我伸手去把她的腿撥開,她卻醒瞭,惺忪瞭雙眼嘟嚨著問我:「你起這麼早啊?」
我回答說:「尿急,我去上廁所。」她說她也尿急,我就說一起去吧,我穿上衣服等著她。
她穿好衣服卻說:「你背我下去!」我站在床前,她跳上背來,暖暖的身子軟趴趴地。
上完廁所又要我背她回來,到瞭樓上,她一直叫著「冷啊冷啊」地鉆進被子去瞭。我想起今天要回傢去,心裡悶悶地。她見我不說話也不上床睡覺,從被子裡探出頭來叫我:「快來啊,還愣著幹什麼?」一邊在被子裡窸窸窣窣地把她的線衫和牛仔褲脫瞭,哆嗦著放到床頭。
我看著她的樣子說:「真有這麼冷嗎?」
她捂緊被子回答說:「是呀,秋天剛起床就是有點冷,一會兒就好瞭。你快進來,兩個人挨著熱和些。」
我脫光瞭衣服鉆進被子去。
她的手像遊蛇一般鉆過來,遊過我的襠部,隔著內褲探瞭一下說:「我就知道你不老實嘛,都這麼硬瞭,還磨磨蹭蹭的。」
我閉瞭眼,她的手在我身上靈活柔軟地遊走,遊過我的小腹,遊過我的胸部,遊過我的乳頭,找到我的手,拉過去貼上她的胸,軟軟的彈彈的,指尖一觸碰到這團溫溫的肉團,她就像觸電瞭一樣顫抖起來。
我爬起來俯下身子,親吻著她的額頭,噬咬著她的耳垂,舌尖劃著她的臉頰……
清晨的微光下,她的臉上泛起瞭紅暈。我找到她的嘴唇,把舌頭伸瞭進去,舌尖纏繞在一起。我用力貼緊她的嘴唇,不留一絲罅隙,隻剩她的鼻孔在「呼哧呼哧」地喘氣。
我深深地呼吸瞭一口氣,她的舌頭香軟糯滑,鉆進我口裡來。我飛快地含住它的舌頭,往外牽引,貪婪地吮吸著她的味道她的甜甜的唾液。
她「嗚嗚」著把手向下摸索,握住瞭我那碩大的欲望之根,笨拙地套動,肉棒在她的溫熱柔軟的手掌變得無比堅硬,絲絲液體從馬眼流溢而出,浸濕瞭她的手掌,黏黏滑滑地串上來奶酪的香味。
我離開瞭她的唇,嘴唇靠近她瞭的乳房,她突地擡起頭來,媚眼如星地看著我急急地說:「你要舔它!」
我沒有回答她,含住乳尖吮砸起來,她無望地把頭倒下去,她嚶嚶地說:「不要,我不要,快停下!」那聲音綿綿的無奈而歡娛,卻聳動瞭胸部雙手擠弄著那鼓脹迎合著。
我用舌尖舐弄她身上唯一一點粗糙的皮膚,這顆玫紅精致的櫻桃是如此的美妙,像有魔力一般讓我的舌尖顫動不已。她的身子像水蛇一樣,在被子裡難受地扭動。她的手繞過我的雙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背,指甲都快陷進瞭我的肉裡,心裡滲滿瞭汗。
她幾乎是急切地說:「我要,我要,我要。」
我把手去探她的濕處,那裡已經淋漓一片,正中花心的時候,她全身一陣痙攣,柔聲的說:「輕點兒」。
手指撥動著肉蕾,一股暖暖的勁兒,順著手指彌散開來。再往裡進去越來越緊,那話兒一陣一陣的動著,往裡進去越來越緊,她的股間已是愛水流溢,一塌糊塗。
我的女人分開雙腿,任由我的指尖蹂躪著她,她粗野地嬌叫:「快受不瞭啦,癢死瞭,快放進來,進裡面來!把你的雞巴放進來。」
終於是時候瞭。我起身翻下床,赤腳踩在冰涼的地板上,指尖帶起的一絲黏液,在晨光裡發著微亮淫靡的光。
她在被子裡擡起頭,用她那雙大眼睛大惑不解地看著我說:「怎麼下去瞭?」
我像頭發瞭瘋的野豬,一下把被子掀翻,她那完美的赤裸裸白花花的身子裸露在我面前,被子裡的熱氣一下子騰發出來,空氣裡彌漫瞭少女的乳香,夾雜著體液腥香的味道。她趕緊懷抱著雙乳,我抓住她的腳踝,把她拖到床邊,她像隻受驚的兔子驚恐地看著我,不知道她的獵人要幹什麼。
我站在床沿,擡著她的渾圓肥白的肉臀,挺著粗壯的話兒,直抵抵地對準那鮮潤欲滴的口子直塞進去,微微的進瞭點兒,我往前進瞭一步,聳身直搗黃龍,全根沒入,比冉老師的緊多瞭,不過柔滑過之。
她「啊」地一聲叫瞭出來,喘息定瞭。
她擡起頭來問我:「這就是那本書上看到的?」
我不敢對視她的目光,沉聲說:「恩!」
她央求我說:「你要輕點,慢點兒,我受不住。」說完倒下去攤開兩手反抓著床單,準備好瞭接受沖撞。
我拾起兩條蓮藕似的修長的玉腿放在肩上,用手抱住,開始慢慢抽動起來,我的女人低低的喊著,那聲音宛若泉眼的嗚鳴。胸前兩個雪白的奶子也隨著前後波動,渾圓堅挺,像兩個裝滿水的氣球。
我緩慢地來回抽送,可是她總不得要領,滑出來好幾次,我想起冉老師當時好像是把臀部擡高,聳動著迎合,我便低聲地告訴她:「把屁股擡高點,我進來的時候,你要聳過來。」
她「恩」瞭一聲,把臀部稍稍太高瞭一點,果然我在那裡面就不在憋屈瞭,抽動也更順暢瞭。她屁股也會往前聳瞭,每一次過來,都把我深深地吞沒瞭,我的蛋蛋撞得濕淋淋的,打在她的會陰那裡,「啪啪」地清響。
不大一會兒,她就熟絡起來,熟悉瞭我撞擊的節奏,敏真的是秀外慧中,冰雪聰明。
她喃喃地囈語:「你可以再用力一些,再快一些。」
我的女人已經不再滿足。我便開始用力抽送,縱橫捭闔,大進大出。
敏也不顧房東是否聽得見,開始大聲吟哦起來:「啊……啊……啊……喔……哦……哦……噢……」,肉饅頭的鮮紅口子剛剛陷進去,又被拉扯著披翻出來,發出響亮的「噼噼啪啪」的聲響。
也不知道抽瞭多少下,天已經大亮瞭,遠處傳來雄雞的啼叫聲,院子裡的梨樹上傳來小鳥的喧鬧聲。
敏滿足地叫喚起來:「我快到瞭,就要來瞭,用力啊,用力……」喊聲撕心裂肺。
我抖擻精神,盡力聳身向前,敏緊蹙著眉,伸長脖頸不停地難受地甩動,青筋凸現,夾緊雙胯,抽搐著,她的雙手還在死死地抓住床單,床單是我壓在床墊下的,都被她扯得皺縮起來。
我越抽越快,越抽越快,她的叫聲越來越大,越來越急促。
終於她緊繃瞭身子,長長地叫瞭一聲:「啊……」,像爬一座很高的山峰,到瞭山頂那種愜意的懈怠。
我感到自己那裡像什麼東西緊緊往裡吸附。說時遲那時快,我趕緊抽身「噗通」一聲急退瞭出來。幾乎同時,一股熱流在小腹湧動著,濃濃白白滾燙的精液「刷刷」噴濺出來,「啪啪」射在地板上,床單上也是,還射在我女人的大腿上。
我閉著眼,身體就像斷瞭線的風箏,飄飄揚揚地飛瞭起來。那張鮮艷的嘴巴也在一張一合的喘動,一股白色的巖漿急急地「咕咕」冒出來,緩緩的蜿蜒流過她的會陰,流過她的肛門,滴落在床單上。她還兀自揚著雙腿,在那裡大口大口的呼吸,直到她徹底癱軟下來,像一株被砍掉的在太陽下曝曬後的瓜蔓。
我到方桌上把紙巾抓過來,先給她那裡擦幹凈,又把她的大腿擦幹凈,床單上的也擦瞭,才把自己的清理瞭。我俯下身把她軟癱癱的身子抱起來,放到床上蓋好被子。
感覺自己倦怠萬分,也赤條條的鉆進被子貼著她躺下,她挨過來往我胸懷裡鉆,像隻被寵壞瞭的小貓。
我問她:「爽吧?」
她綿綿地說:「爽死瞭,你就是個色中餓鬼,那書上的你都學會瞭?」
我有點得意地說:「恩恩。」
她驚喜地說:「真的呀!我要你每天換一個姿勢日我。」
我禁不住搖起頭來:「那怎麼行?書就隻有那麼多頁,你還活著那麼久。」
她無賴地說:「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要你換你就換。」
我無可奈何地說:「好吧,好吧,天天給你換。」……
在被子裡笑鬧瞭一回,我就迷迷糊糊地睡去瞭。我做瞭個夢,夢見我聽見上課的鈴聲瞭,我著急地跑下床,慌亂地穿衣服,找書包,急匆匆地往學校趕,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到瞭教室門口,猴子班主任正在黑板上寫著什麼,下面同學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抄著,班主任一回頭看見瞭我,大叫起來:「起床瞭,起床瞭……」,睜開眼卻是敏在床邊叫著我起床。
我趕緊爬起來問她幾點瞭,她說快十一點瞭,我的天吶,我隻有二十分鍾的時間,如果我趕不上來鎮上趕集回程的拖拉機,我就得走著回去瞭,這淅淅瀝瀝的山路要走兩個多小時。
敏見我忙亂的樣子,也幫著我去整理被子,她一邊整理一邊問我:「你好久回來呢?」
我說:「明天吧!」
她又問:「什麼時候?」
我告訴她:「早上就回來。」我真的一刻也不想離開她,我想盡快的見到她。
她擡起床墊把被單扯下來折好,對我說:「我拿回去洗幹凈瞭給你,濕瞭好大一片,誰叫你射那麼多?」
我哭笑不得:「你還不是射瞭那麼多!」
她掄起粉拳給瞭我一拳:「還不是你給弄出來的。」
我沒時間和她理論,背起她就匆匆下樓瞭。到瞭街口我們就分手瞭。還好,那輛翻過幾次車的垃圾拖拉機還在,上面已經擠滿瞭人,車欄上吊著人,車頭上也是人。我跳瞭上去,拖拉機顛顛簸簸出瞭鎮子,像隻老邁不堪的病怏怏的牛,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東倒西歪地前進。
天空飄過幾朵烏雲,又有稀稀疏疏的雨點飄灑下來,我的心情又變得沉重起來,陷進輟學的泥潭中不可自拔。遙遙望見蒙蒙霧雨中飄著裊裊炊煙的村子的時候,我告訴自己要振作起來,昂首挺胸,面帶笑容,跟往常一樣,可是這破車搖搖晃晃就是不願抵達,這段路突然變得好長好長,我不得不一次次在心裡默念:「振作起來,昂首挺胸,面帶笑容……」,一遍又一遍。
謝天謝地,拖拉機終於在場壩中央停瞭下來。這個場壩在村子的中央,平時村裡開會,村民們曬谷子、打谷子、趕集……都在這裡進行,那也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地方,到瞭晚上月明之夜,這裡就是我們狂歡的場所。
一進傢門,媽媽正在廚房忙得個不亦樂乎。爸爸靠著柱子坐著,翹起二郎腿「撲通撲通」地抽著水煙筒,煙霧騰騰,他抽起煙來是看不見我的。
我走到媽媽身後伸長脖子看她在做什麼,她轉頭看見瞭我說:「來瞭也不出個聲!像隻貓似的,你看我給你做瞭什麼。你最愛吃的豆花呢!回頭我用油炸瞭豆腐塊,你帶到學校吃。」
我才發現,回到傢,笑容是那麼的容易綻放,爲瞭掩飾我心中的不安,和爸爸說瞭幾句話我就借口看書上樓去瞭,拉本書過來翻開放面前,傻傻地發愣。
我記得小時候,墻壁都沒有,我和爸爸睡在這閣樓上,都可以看見天幕上的繁星,對於童年的我來說,晴朗的夜空是那麼深邃那麼神秘,爸爸總愛把我攬在他粗壯結實的臂彎裡,教我認天上的星星,告訴我最亮的那顆是啓明星,北鬥七星的柄總是指著北方……那拖著長長的尾巴掃過天際的星星叫彗星。
那時的爸爸是健壯的,勇敢而毫不畏懼的。隨著我越長越大,爺爺越長越老,爸爸臉上的的笑容越來越少瞭,後來爺爺死瞭,爸爸就一下子老瞭許多,幾乎難得見他一笑,取而代之的是少有的嚴厲。他跟我說天上的一個星星代表著地上的一個人,地上的人死一個,天上就有一顆星星落下來。
媽媽在叫我瞭,飯做好瞭,我就下樓去吃飯,香噴噴的蔥油豆花,澆上紅紅的辣椒醬,我打小就愛吃這個,一下胃口大開,吃瞭三大碗飯。
我就不明白,爲什麼後來的日子我就吃不到這麼好吃的豆花瞭,我天南地北到過不少地方,吃過不少豆花,卻再也找不回記憶中的那種味道。
媽媽看著我狼吞虎咽的樣子,心疼地說:「你呀,一個人在外面,飯都煮不熟,別說做菜瞭,別談吃什麼好的瞭。」
我深以爲然。飯吃飽瞭,爸爸問起我在學校的情況,我都說跟以前一樣,很好很好,跟以前一樣就說明我還是第一名。
爸爸想要再細細問下去,我怕露出破綻,借口要上廁所,飛快地走瞭,回來直接上樓瞭,在閣樓上坐也不是,睡又不成,焦灼莫名。
爸爸還在抽他的水煙筒,過瞭好久才出去瞭,我趕緊下來跟媽媽說我要走瞭,媽媽顯得有點驚訝:「不都是星期天走的麼?」
我告訴她:「學校明天有個小活動,要開會的哩!」
我還是撒謊瞭,媽媽看起來沒察覺我有什麼異樣,就去給我準備平時帶的生活材料,像往常一樣。
外面的雨還是綿綿地下個不停,我手裡拿把傘打著就往表叔傢去瞭,他有一個大貨車,我去問他要不要去樓下拉煤,順便捎我一程。
他說路太滑,去不瞭啦,不過他聽說他有個朋友要去鎮上,不知道走瞭沒有,不過是馬車,如果我願意坐馬車的話,他可以幫我問問。
我有什麼不願意的,這鬼天氣,有坐的就不錯瞭,總比走路要強。
表叔的朋友很義氣,直接把馬車開到傢門口來接我,還幫我把東西搬到馬車上,母親一個勁地說謝謝,連我都覺得她過於客氣過於囉嗦瞭。
馬車夫戴著鬥笠坐在車頭握著韁繩,我打著傘坐在車的中央,油紙佈蓋著車上東西,好讓雨水不會浸濕瞭。一聲唿哨,一記鞭響,在蒙蒙細雨中,我們上路瞭。同樣的搖搖晃晃,同樣的崎嶇不平,同樣的緩慢悠長,可是真奇怪,我的心情意外地大好……
沒有瞭拖拉機冒著黑煙的發動機令人作嘔的轟鳴聲,沒有瞭不同氣味的人推搡叫罵。有瞭馬蹄鐵落在地面上有節奏的踢踏聲,車輪碾過的路面發出的黏稠的聲響,還有馬車夫那幾嗓子粗魯的歌謠:
……十月梅花夢花郎,夢見同睡又同床。一時不見郎的面,郎也慌來妹也慌。冬月裡來雪花深,外面來瞭情意人。情妹來瞭心喜上,今晚一定要成群……拖聲擺氣的唱,唱得聲嘶力竭,這節奏讓我太喜歡。我也想有匹馬車,沒日沒夜的駕著,漫無目的地前進,讓我的歌聲也飛揚在細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