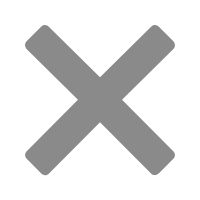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八章
我走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用力用力地低著頭。此時此刻在這個學校,如果非要說還有什麼人是值得我留戀的話,這個人非王老師莫屬。
我從來這個學校的第一天開始,就認識她瞭。那時正是入學考核剛剛結束的晚上,下著綿綿的秋雨,溫熱的夏意還未退去。我正在閣樓上靜靜聽這天地間的微鳴,沙沙的聲音讓我沉醉。
有個同一個班老鄉跑到院子裡來叫我,我下樓來,他說英語老師叫我過去一下。我那時還不知道王老師是個女的,我和她一同去見王老師,那是王老師還住在一個池塘旁邊的居民傢裡。我們沿著池塘邊潮濕的小路摸索著找到瞭這傢住處。
一個二十多歲女子走到院子裡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最漂亮的年輕女人,心裡嘖嘖稱奇。進瞭屋子裡,我見她把烏黑油亮的頭發紮成兩條羊角小辮,整齊的劉海像菊花的花蕊那樣彎曲在彎彎的細眉之上,上身穿著一件薄薄的白色線衫,下身穿黛青色的長褲,美麗而不妖冶,嫺靜而大方,腳上穿著一雙淡紫色的拖鞋,雪白的腳丫子露出來,呼應著白皙的面龐,身段修長勻稱,卻又讓人覺得不乏女性美所必需的豐滿;皮膚是那種嬌柔的淡淡白,像梨花的顏色……
一雙活潑潑的大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夢幻似撲閃著,眼仁像外面漆黑的夜,仿佛會不分晝夜永不停息地撲閃下去,總帶著甜甜的安詳。身軀纖細而不瘦削,周身上下都顯出嫵媚動人的沉靜,頗有幾分古典美女的韻味,隻有眼睛異樣地活潑,甜甜地一笑,兩邊臉上便露出迷人的小酒窩,那笑像一陣帶著香氣的微風,讓人迷醉。
我突然想起在批鬥大會上「臟臟」說敏是新學校的校花,對這點我一點也不知情,她也未曾提起,也許她真的是吧,她身上確實散發著奪人的光芒,那是和王老師的美迥然而異的,敏那麼張揚,急切地想表現自己,王老師則含蓄淡然,如果說敏是一朵粉嫩嬌艷的初生的玫瑰花,王老師則是那淑靜淡雅的梨花。不知有多少色狼對著王老師流過口水呢,想著「臟臟」淫穢的舔舌頭的樣子,我心裡泛起一陣惡心。
王老師叫我來是告訴我我的英語考試結果是第一名,她說如果再細心點的話,是可以得到滿分的,並在試卷上給我指出瞭我的錯誤,她說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錯誤,不過可以看得出我性格比較急躁,這讓我心服口服,確實如她所說。
空氣越來越沉悶,北邊的天空先是飄過來幾朵烏雲,風輕輕卷起地上地塵土飄揚著,不大一會兒,黑雲遮蔽瞭太陽,籠罩瞭天空。我知道要下雨瞭,可是我真的不想回去。我坐在麻將館的對面的石凳上,對面有個瞎子老頭在拉二胡,琴聲悠揚淒切,如泣如訴,把人心裡的肉拉得都悸動起來。秋雨老是遲遲不落,我希望上蒼普降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雨,也許這樣我會好受些。
雨落下來瞭,稀稀拉拉地一陣風似地,隻是打濕瞭街道,打濕瞭房頂,甚至不能打濕我的衣服,這讓我大失所望。吹來的風有瞭涼意,正應瞭那句俗話「一場秋雨一場涼」,我感覺到有些冷,抱著雙臂卷縮在墻角,拉二胡的老頭也不見瞭蹤影,沒有瞭他的琴聲,天空的陰雲在灰色的天幕上過來一朵又來一朵,絡繹不絕,無有休歇,我更加顯得寂寥無聊起來。
明天就是星期六瞭,我回去如何和爸爸媽媽說,而最要緊的是眼下就要放學瞭,敏一定會來找我,我如何跟她說,我可不想失去她。沒有書讀瞭,難道我就一直這樣,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面對何去何從的問題,這問題是這樣地讓人苦惱,讓人如此痛苦不堪,讓人昏昏欲睡。
也許我該去新學校問問他們要不要我,運氣好的話也許會要的吧,可是我又沒有錢,這多出來的錢要回傢跟爸爸要,那這事情就暴露瞭。要新學校接受一個被老學校扔出來的垃圾還不收錢,這是無法想像的事情,何況現在我是如此的無精打采。
本來我還想等放學的時候去新學校門口等著,找到我的女人,或許我能從她那裡得到一些安慰,哪怕一點點也好,可是我真的是太累瞭,我需要好好地睡一覺。我得回去瞭,在經過雜貨鋪的時候,沒頭沒腦地進去亂翻一通,,雖說是雜貨鋪,也賣一些老黃歷和別人用過的資料或者舊書。
在這些雜亂不堪的廢棄物中,我看到一本殘破不堪的線裝書,大概叫什麼經,管它什麼經呢,古香古色地,瞅著甚是喜歡,就想買瞭。老板非要把這本破書說成是古書要賣十塊錢,我也不想和他討價還價,而且我也不在行。甩瞭十塊錢給他,還大方地叫老板別找零瞭,老板在後面罵罵咧咧地說:「神經病哩。」
我幾乎是夢遊一般地回到閣樓上,回到瞭他們稱之為的滑稽可笑的「狀元樓」,衣服也沒脫,蒙頭便睡,什麼猴子班主任,什麼「臟臟」,什麼「冉老師」……都給我見鬼去吧,什麼玩意。
我以為我一定是在敏的呼喚聲中醒來,可是卻沒有如我所想。我醒來時夜已深沉,周圍是無窮無盡的黑暗,肚子咕咕地叫,餓得要死,廚房那用粘土糊的用煤的爐灶,估計早已熄滅瞭,可是現在也沒人會賣小吃瞭吧,我得把火生起來做飯把肚皮填飽。
我伸手去拉燈線的時候,碰到一團軟軟的肉,這可嚇得我不輕,倒吸瞭一口涼氣,難道是我剛睡醒醒神志不清產生瞭幻覺,難道我還在夢裡,剎那間睡意全消,心裡「砰砰」地跳個不停。
我顫抖著再次把手伸過去,我的天啦,還熱乎乎的在動著呢,所有小時候從爺爺那裡聽來的鬼故事一下從腦袋裡冒出來,我驚悸得大叫一聲:「鬼啊!」
這隻鬼突地跳起來,「啼嗒」一聲把燈打開瞭,我還以為是誰呢,這妮子。
敏看見我神不守舍驚慌失措的樣子,笑得直不起腰來。房東也起來瞭,「噔噔」地上樓來,我也清醒瞭好多,敏驚惶地給房東打招呼:「舅姥爺好!」
房東對著她點瞭點頭問我:「這是怎麼回事?」
敏又開始笑起來,我趕緊搶著說:「爺爺,沒事瞭,我做噩夢瞭!」
房東嘆口氣說:「嗨……這麼膽小!我活瞭這把年紀,都沒見過鬼的,我以為你真遇見瞭,趕緊上來也開開眼界,下次要是真遇見,你可給我抓牢瞭啊!」
房東的幽默把我們緊張的心情打消瞭,我原本以為他看見我們兩個在一起他要罵我們的呢。
房東下樓去瞭,臨走時回頭說:「兩個早點睡吧,大半夜的嚇人兮兮的。還有,不要把樓板給我整塌瞭!」
這個老不正經!我聽見小寡婦在問房東怎麼回事,房東說:「做噩夢呢,這小子真行,把我外甥女給搞瞭,兩個睡一張床上呢。」
小寡婦說:「這麼大的孩子,毛都沒長齊,懂個屁啊!」
敏聽到這裡,惡心地小聲說:「呸!這女人是個騷貨。」
管她什麼騷貨不騷貨,我的肚子餓得不行瞭。我爬起來準備下樓,敏問我幹嘛去,我說肚子餓瞭做飯吃,敏咯咯笑瞭:「以前你一個人自己做吃的,現在我都是你的人瞭,你還自己做,你當我不存在啊?」
我有點難為情地說:「你不知道米啊菜啊的放哪裡嘛!」
敏氣惱地命令我說:「你說你想吃什麼,我給你露一手。」
我說:「蛋炒飯。」
敏不屑地說:「我還以為你要吃什麼山珍海味,蛋炒飯嘛,小菜一碟。去把米和蛋找出來,還有辣椒和蔥。」
我奉命下樓去瞭,還好廚房裡的火不但沒熄滅,還燒得挺旺,大概是房東回來重新添煤瞭。
敏跟著穿好外衣就下來瞭,我跟她說:「大廚師,這裡就交給你瞭,我有點困,先躺會兒。」她白瞭我一眼,我就上樓來瞭。
我到瞭樓上,才發現那本破舊的書落在床腳,我才想起我白天買瞭一本書,我撿起來摔到方桌上就睡瞭,經過這一番鬧騰,怎麼努力也睡不著,廚房裡傳來鍋瓢碗盞的觸碰聲「叮叮當當」地響個不住,我百無聊賴爬起來到方桌上把那本書拿過來,鉆進被子裡看,封面已經皺皺巴巴的瞭,隱約看見書名叫「素女經」,都是繁體字刻印的樣子,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就隨便翻瞭一下。
我的天,裡面的字密密麻麻的,全是刻印的豎排繁體字,紙張泛黃得仿佛稍微用點力就要碎裂似的,心裡懊悔不已,十塊錢對那個年代那時的我來說可不是個小數目,十塊錢可以買讓我坐拖拉機回傢十次。
不過買都買瞭,也隻有這樣瞭。繁體字我也認得不少,小時候看爸爸的書,什麼《三國演義》《紅樓夢》《紅巖》都是繁體字印刷的,不過是橫排罷瞭,這豎排不斷句,看著好不習慣,還是先看看有沒圖吧。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這是傳說中的「黃書」呀,裡面的的線描圖畫的小人兒都是「妖精在打架」,赤裸裸地讓人面紅心跳,原來古人也好這一口呀!
原來我和敏做的那些姿勢是有名目有來由的,都可以在裡面找得到,我好奇地仔細地看瞭一下,裡面起的名字簡潔而傳神:昨天下午在閣樓上幹的姿勢叫「龍翻」,確實有點那個意思,像蛟龍一樣翻滾聳動;到瞭晚上在田裡她騎坐在上面的姿勢叫「魚接鱗」,怎麼想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多年以後才知道是魚交配的姿勢;
冉老師擺出的姿勢叫「猿搏」兩猿相搏,一猿得手而執對方之腳,看來冉老師是個「練傢子」,做起來這麼舒服,說不定她也是在這上面看來的,到時候我得問問她看是也不是;站著幹的姿勢怎麼找也找不到,我還以為是缺頁瞭,翻瞭好幾遍,仔仔細細地查看書縫有沒有撕裂的痕跡,還是沒有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原來我還獨創瞭一式,這個發現讓我覺得有點得意,原來古人也不是什麼都知道的嘛。
正在我暗自得意的時候,敏已經大功告成,正「噔噔」地走上樓來,嚇得我趕緊把書塞在枕頭下面。我故作鎮定,討好地笑著說:「聞著真香,就是不知吃起來味道如何瞭?」
敏嗔怒地說:「愛吃不吃,不吃拉倒,還挑三揀四的呢,這才幾天呀,就翹尾巴瞭?」
我燙瞭臉不敢說話瞭,我問她:「什麼時候來的?」
她說:「一放學就過來瞭,叫人也沒人應,我就自己上來瞭,看見你睡得正香,我就做瞭作業,作業做完瞭你還沒醒,我又看瞭書,看瞭書你還是沒醒,我也有點困瞭,就睡瞭。瞧你那膽兒,這樣就嚇著你瞭?」
我爬下床來接過碗吃起來,她說她也餓瞭要我喂她,我就像老鳥喂小鳥那樣一口一口的喂她,自己也吃,不一會兒她就說飽瞭,我把碗放在方桌上(那方桌我是兩用的,既在上面讀書寫字又在上面吃飯),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不料敏早覷瞭空子,從枕頭下把那本書拿出來,坐在床沿翻看。我一回頭看見瞭,趕緊伸手去奪,不料撲瞭個空,我看到她正翻到那圖瞭,不顧一切把她壓住,去手上搶奪。
敏得意地說:「這可讓我逮住瞭,我還以為你那麼認真用功呢,還哄我說上來睡覺,原來在看黃書呀……」
我有點惱羞成怒瞭,氣哼哼地把書搶過來甩在方桌上,不理她瞭,繼續吃飯,敏見我真的來氣瞭,試探性地說:「我就說不可能一上手就會嘛,一定有人教你的。」
我白瞭她一眼,她更得意瞭:「還好不是別的女孩教的,還是得謝謝這本書,把你教得這麼棒。」
我真是百口莫辯,沒好氣地說:「我又沒看,我是今天在雜貨鋪買的。」
她真是個得理不饒人的傢夥:「還在狡辯,真是'鴨子熟瞭嘴還硬',書都被你翻得破成這個樣子瞭,你真是用功的好孩子啊!」
得瞭,我服瞭,我認瞭,這麼伶牙俐齒的女孩我還是第一次見,不知道怎麼應付這種局面,隻好默不作聲自顧自地吃飯。她見我不答話,自己脫瞭衣服鉆進被子裡睡瞭。我吃完飯出去上瞭個廁所回來,她正睡的正香呢,看著她孩子似的天真的臉,覺得又是疼愛又是難過。
我輕手輕腳地把衣服瞭脫瞭,鉆進被子在她旁邊睡下瞭。可是我怎麼也睡不著,白天發生事歷歷在目,明天是星期六,我就要回傢瞭,我在為到底跟不跟父母說這事兒發愁呢。從小到大我都沒對父母說過謊,也許我有一種選擇:什麼也不說,就像平常回傢一樣;不過這種選擇對我來說有點困難,我是個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的人,是個藏不住沒有深度的人,如果我愛一個人,臉上就是討好的諂媚;如果我恨一個人,眼裡便射出巴不得把人吃掉的兇狠的光。
不過除瞭這種選擇,我還有別的選擇嗎?如果告訴瞭爸爸媽媽,這種後果我連想也不敢想,小時候我犯瞭一點點錯,爸爸那深惡痛絕語重心長的話語,讓我覺得我不僅僅是犯瞭大傢都會犯的錯,而是犯瞭關乎道德的不可饒恕的罪。這種感覺讓我討厭自己,喘不過氣來。
如果我說謊呢,媽媽那善良的眼神能洞穿一切,她一定會知道我說瞭謊,很多次我試圖開始說謊,都被提前警告而告磬。如果我選擇我不說話的話,好壞並存,好處是我不用說謊瞭也不會受到譴責,壞處是他們一定會懷疑但是不確定,那就讓他們懷疑好瞭,兩害相權取其輕,打定主意:無論怎麼問我我都不說話,裝著跟平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