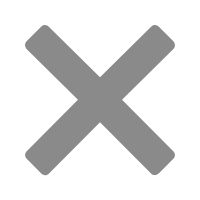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七章 猴子和蝴蝶
我醒來天已大亮,她已經走瞭,我想著我這個夢,心裡黯然不歡。時間已經不早瞭,我匆忙地洗漱完畢,飛快地背上書包就去上學瞭。
這天是個特別的日子,空氣中浮動的不安讓我捕捉到瞭……下瞭早自習,我似乎感覺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偷偷地看著我,竊竊地在討論著什麼。隻有幾個跑過來打招呼,他們都是和我從一個村子裡出來的,小的時候是玩伴,他們也沒有說實話,隻言片語,說得含含糊糊,不甚明瞭。
第一堂課成瞭批鬥大會,班主任一上講臺就叫我站起來,我就站瞭起來,他厲聲問我:「昨天去哪裡瞭?」
我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麼大的火,不過我從來跟老師就尿不到一個壺裡,並不是我天生仇視老師,我沒有這種惡劣的性格,我隻是跟他們沒什麼說的,見面也隻是禮貌性的問候,不像有的人跟在老師身邊屁顛屁顛地討好他們。
班主任尖嘴猴腮的樣子真像一隻猴子,這不是我一人這樣覺得,還有人說他以前就是偷雞摸狗的幹活,穿件衣服臟兮兮的,蓬亂的頭發掛滿蝨子的蛋,像冬天下瞭的雪粒,在他頭上沒有化去,我記不得是誰說的瞭,雖然我覺得現實生活裡不會這麼誇張,但是確確實實讓我一直很討厭他,而他現在就站在那裡,氣鼓鼓地腮膀都紅瞭,細小的眼睛裡射出嚇人的光來。
我不知道我究竟做瞭什麼,我告訴他:「我回傢瞭。」
下面一片譁然,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都這麼大反應,有幾個人聲音特別大,我看到瞭那個女孩的哥哥尤其興奮,就是初二的那個女孩,他哥哥叫張章,在我們那裡沒有翹舌音,我們常常看見小孩把衣服弄臟瞭都會跑到媽媽跟前叫「臟臟」,就是那個音,今天我看他特別激動特別不順眼。
班主任再次發話瞭,音調並沒有降下來:「你好意思說你回傢瞭,你把我的話當耳邊風是不是?」
下面鴉雀無聲,我知道有的人被這嗓門震怕瞭,有的人在等著看好戲……
我一臉茫然等著他繼續發飆,他叫起來:「同學們,我看他是記不得瞭,給他說說,我昨天說瞭什麼?」
一片整齊的聲音像約好的一樣,又像是莊嚴的宣誓:「修路!」
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昨天在課堂上,一整天我都在想著我的女人,想著和我的女人幹那事,什麼也記不得。
這整齊的應和聲鼓舞瞭班主任,他脖子伸得老長,青筋凸起,像極瞭一直準備戰鬥的公雞,他吼著:「聽見瞭吧!全班人都知道下午要修路,就你一個人不知道?!」
唾沫星子飛濺出來,射在前排同學的臉上,好幾個被射到的同學伸手把它抹去,我想起我把精液射到我女人的肚皮上,如此相似,嘴角禁不住浮起一絲微笑,他可能誤會瞭這該死的來得不是時候的微笑,憤怒驟然升級,他的整個臉都變形瞭:「滿不在乎?滿不在乎是不是?!」
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停瞭停,想瞭想繼續吼叫:「你不要以為你是第一名,就可以搞特殊,大傢都在熱火朝天地搬水泥砂漿,背石頭,你就那麼嬌嫩,你就是大爺?」
我同桌的瘦小的女孩拉瞭拉我的衣角,輕聲地提醒我:「認錯,快認錯!」
我的身子被她扯得歪瞭一下,我低頭看瞭她一眼,她的眼裡滿是恐懼,滿是哀憫,滿是哀求。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無明烈火,讓我怒從膽邊生,我不再是唯唯諾諾任人屠宰的笨豬,我義正詞嚴的回答瞭他:「我不是來修路的!我是來讀書的!我不是被強迫的義工!」
我的聲音沒他的大,但是清晰得足以讓在教室裡的每個人都聽得清楚,大約有那麼一兩秒,教室裡靜得可怕,班主任的臉刷地紅瞭,繼而暴跳如雷:「這是我的地盤,我說瞭算!」
這活脫脫就是個強盜!就是個山大王!他停頓瞭一下,穩住瞭情緒,嘶啞著嗓子叫起來:「今天,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我們投票!同意這個害群之馬呆在這班裡的,舉手!」
我根本就不想預料這結果,我看到有的人才舉到一半又放瞭下去,不過還是有個人的手舉瞭起來,跟著像雨後的春筍那樣舉瞭起來,班主任氣呼呼地點數:「一、二、三、……、三十。」
我不知道怎麼會是這個數,全班六十個人,剩下的就不用數瞭,這是個一年級的數學題,除開我等於二十九,還有請假沒來的、遲到曠課的和棄權的。他也大聲宣佈瞭他的演算法,隻是沒告訴同學們是假設全到全齊的情況下,他氣紅瞭眼:「剩下二十九,還有我沒投呢!剛好一半,算你運氣好!」
他還是氣呼呼的,不過就像隻斷瞭翅膀貓頭鷹,在講桌上踱來踱去,一揮手做出瞭決定:「大傢自習!我去向校長反應情況,回來告訴你們結果。」
說完就走瞭,教室裡炸開瞭鍋,「臟臟」把他討厭的臭豬頭頭伸過來,陰險地大聲說:「我看到你瞭,你玩女人去瞭!你昨天下午和新學校的校花走在大街上。」
我直直地盯著他,他還在怪聲怪氣地說:「幹瞭沒有啊?滋味如何?」
我一把把他的頭發抓住,扯過來按在桌子上,掄起拳頭想砸死他,幾個一起從村裡出來的老鄉抱著我不讓我打他,我用力太重瞭,他的嘴角流出血來,他一邊揩著血沫子一邊說:「我有你好看的,你等著!」
一個老鄉在耳邊說:「別惹他,他爹是教育輔導站的站長,校長都聽他爹的。」
我怒氣未消,氣不打一處來:「我日她媽,他就是我小舅子,他爹來我一樣打死他!」我從來沒打過人,這是我第一次對別人動粗。
班主任終於回來瞭,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去見瞭校長呢,還是隻是去上瞭一個廁所,「臟臟」迫不及待地沖到他面前告我的狀,像隻狗那樣,班主任很認真地聽取瞭他的「證詞」,也不用旁證,迫不及待走上講臺宣佈:「校長說瞭,這事由我一人做主,數罪並罰,打架曠工,立即開除!」
我愣住瞭,這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去哪裡,班主任對著我一揮手,像毛澤東指點江山那樣的氣勢,吼叫著:「滾!」
這一聲巨雷,多年後還在我的耳邊回蕩。我知道我必須勇敢,我必須被逐出校園,我背上書包,抬起頭走出瞭教室,兩條腿想被灌瞭鉛,如此的沉重,好不容易出瞭校門,下課的鈴聲驟然響起。一個小人,一個強盜,一次約會,一次修路,就把我給放逐瞭,我像隻被主人逐出傢門的狗,疲憊走在大街上。
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孩子,從學前班到現在,還沒有老師對我這樣吼叫,他們隻會鼓勵我贊揚我。我突然很想我以前的老師,雖然我沒有在他們那裡學到過有用的或者沒用的東西,我成績好來自於我的努力,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對學習有著瘋狂的迷戀,就像此刻我迷戀我的女人一樣。方圓十裡,我是大傢交口稱贊的好孩子,傢長把我作為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樣,老師把我作為督促同學的教材,而今天,我竟被如此荒唐地驅逐瞭。
這個淒慘的消息是不能被媽媽知道的,我想起我小時候調皮她都會哭,這個消息絕對會讓她嚎啕大哭。爸爸也是不能讓他知道的,他是我真正的老師,一個破落地主的兒子,有著高過村裡任何人的文化水準和脾氣,結實的肌肉,篤定的兇狠的眼神,他就是個神一樣的存在,我很怕他又不得不聽命於他。我隻是聽見他常常和媽媽說:「這孩子隻是長得像我,脾氣一點也不像老子。」
媽媽這時就會說:「你那脾氣好?要不是我一時糊塗,你老婆都討不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喜歡我這樣軟弱或者堅強不夠的性格。
我來鎮上讀書是減免生,這完全是由於我的成績和學校延續已久的慣例:在招生之前會進行一次考試測評,第一名減免全部學雜費。我以讓人望塵莫及的成績得到瞭這個資格。而如今我失去瞭這個機會,我那時還不能理解「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的這種放達,我覺得我失去瞭我的東西,而且無處申訴,無處傾訴。
我想去見敏,我想找到她,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個班,離放學還要到下午,在這段時間裡我隻能等待,我又覺得不願意見到她,見到她怎麼說呢?說瞭她還會要我嗎?我心裡很矛盾。現在回閣樓去幹什麼呢?什麼也幹不瞭,又不用讀書瞭。
我想起瞭英語老師,或許我應該去跟她告個別吧?從我來學校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認識她瞭,以後的日子她對我也多有照顧。
我轉身向學校走去,我已經討厭那個校門,我沿著校外的墻找到後門,從那裡進去就是教師宿舍瞭,所有的教職工都住這棟二層樓的平房裡,包括校長,包括那個教育輔導站站長……
我學校外的墻下大聲喊:「王老師,王老師……」
王老師並不老,我看她也就二十出頭,是個很漂亮的湘妹子,渾身散發著成熟女性的味道。那個「臟臟」在上英語課的時候常常色瞇瞇地盯著她的背影把舌頭伸出來,像狗吃飽瞭一樣在嘴唇上刷一圈,這讓人真惡心。
我叫瞭好幾聲沒人應,正準備轉身走開瞭,二樓上跑出兩個女人爬在護欄上叫我。我抬頭一看,一個是王老師,一個是冉老師,冉老師是初三一班的,是和王老師一樣的湘妹子,從同一個地方來的,她給我最深的印象是那兩片向上向下翻掀的嘴唇,肥厚的性感,她沒王老師高,五短身材,但是很白。
他們班的學生說她常常在課堂上穿透明的薄裙子,內褲乳罩都可以看得清楚,還有人說看見那裡黑乎乎的一片。我回過頭來,王老師大聲的問我:「怎麼瞭?沒上課嗎?」
我沒說話,有點想哭的感覺,她見我不說話,就叫我上來,我從後門上去到瞭二樓。
王老師笑瞭,臉上泛出她那招牌似的完美的梨渦:「你怎麼瞭?課也不上,沒精打采的。」
我六神無主地說:「我被開除瞭。」
她的笑止住瞭,大半天合不攏嘴,她沒問我為什麼,而是叫我進去她的宿舍,原來她們正在做早飯,她顯得有點不安:「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你,一起吃飯吧?」
冉老師問她:「這就是你們班的第一名?」
她說:「恩,她成績可好瞭!每一科每一次考試都是第一名。」
冉老師咯咯地笑起來:「哇!我怎麼沒教到這樣的學生呢?」
這個女人的笑無形中有種誘惑的力量在裡面,她穿著透明的薄裙子躺在床上,王老師忙來忙去地又是弄菜又是煮飯,她都不會過來幫忙一下,典型的好吃懶做欠操的女人。
我和王老師終於忙完瞭,王老師說:「和我們一起吃吧,隻怕我們傢鄉的口味你吃不慣哦?」
王老師這麼客氣,搞得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我笑瞭:「毛主席老人傢不是愛吃辣椒嘛,我也能吃的。」
冉老師哈哈的大笑起來,潔白的牙齒露在外面,王老師拍瞭她一下她才止住瞭。我沒去過別的地方,不知道別的地方的口味,不過湘菜吃起來還好吃,辣中帶酸,沒想到王老師不光人長得漂亮,還有一副好身手。
吃完瞭,在洗碗的時候,王老師回過頭來問我:「有什麼打算呢?」
我搖瞭搖頭:「不知道啊!可能去新學校吧。」
我確實這樣想過,隻是我連敏都不敢見,那有什麼勇氣去新學校呢?王老師看起來有點傷感:「好好的一個學生,就這樣跑到對手那邊去瞭。」
我看見她眼中閃著淚光,停瞭一會兒,她又說:「去吧!」像下定決心瞭似的長長地嘆瞭一口氣,直起身來把碗上的水滴甩掉,她接著說:「半期考試的結果下來瞭,你的獎狀獎品不要瞭?那麼多張呢!單科第一名全是你,總分第一名也是你,還有軟筆書法硬筆書法第一名,運動會長跑短跑第一名……」
我想起來瞭,全州會考剛過不久,至於運動會嘛,那些嬌生慣養的鎮裡娃兒那裡比得過我,她說:「想不到你跑得還真快,速度'嗖嗖'地像射箭一樣。」
湖南話聽起來真好聽,柔柔的聲調,說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微微地把聲調上揚一下,格外動人,我笑瞭:「嗨,我成天在大山裡追著牛兒跑,擰≠子也跑不過我哩!」
她驚訝地說:「你還要放牛啊?」
我說:「是啊,我從小學就開始放牛,七八年瞭吧。」
她來瞭興趣:「我從小都沒去過農村呢,快給我說說你小時候的趣事。」
我的話匣子也打開瞭,剛才煩悶的心情一掃而光。我給她們講小時候怎樣用樹杈做彈弓打小鳥,怎樣去捅馬蜂的窩,怎樣用秸稈搭造小屋,怎樣玩「過傢傢」,怎樣在水田裡抓泥鰍和黃鱔,怎樣玩耍用樹根做的陀螺……
農村的瑣事在她們眼裡成瞭新鮮的事物,她們一邊聽一邊笑,笑得前仰後合,一邊說:「想不到你是這麼個不聽話的頑皮小孩子。」
冉老師更過分,邊笑邊在床上打滾,掀起瞭裙擺,她雙胯間的鼓蓬蓬的東西展露無餘,被一條淡黃色的三角內褲包裹著,蓮藕一般潔白的雙腿在我眼前晃動,這有意無意的誘惑讓我想起瞭我的女人,想起和她幹的那些事,褲襠你那條蛇慢慢地舒展開來,蠢蠢欲動,我驚慌得不敢站起來,一直坐在椅子上,把臉朝向王老師那邊,避開那活色生香的畫面。
下課鈴聲「叮鈴鈴」地想瞭,王老師叫起來:「唉,我早上還有兩節課,你們玩著吧,等我回來,要是你要走的話,記得回來找我,我還是你的老師嘛。」
說完就在鏡子前梳理瞭一下頭發,往臉上擦瞭點什麼東西,去書架上取來書本,急匆匆地走瞭。冉老師站起來說:「我去上個廁所,馬上回來。」
屋子裡就剩下我一個人,落寞的情緒又湧上來,我走到窗子邊看著天空,初生的朝陽正燦爛著呢,遠處梯形山地上的油菜花在陽光的照射下,泛著生動的金色的光輝。
上課鈴聲響瞭,冉老師幾乎是踏著鈴聲進門的,她隨手把門撞上瞭。我看瞭她一眼,她仿佛是無意的。她還是往床上一躺,四仰八叉地。我繼續看著外面,我也預感到即將發生什麼,房間裡靜得可怕,隻有鬧鐘的清脆聲音在「滴答」作響,跟心跳一樣的節奏。
她突然開口說話瞭:「太陽的光好強,能不能幫我把窗簾拉上呢?」
我拉上窗簾,走到椅子上坐下,椅子正好面對著床,我也面對著她瞭,她直起身來,我趕緊把盯著她的目光轉移瞭,她說話的聲音突然像變瞭一個人:「好熱啊!」
我眼角的餘光看見她理瞭理頭發,把肩上的裙帶從肩上松垮下來。我再也坐不住瞭,突地站起來沖到床前把她撲到在床上,她大叫起來:「你幹嘛呢?你幹嘛呢?」
我突然恐慌起來,怕人聽見,我用嘴堵住她的嘴不讓她叫出來,她發著「嗚嗚」的聲音拼命地掙紮,緊閉牙關,死活不讓我的舌頭伸進去。
這樣對峙瞭很久,雙方都滿頭大汗地喘著氣,我真的想奪門而逃瞭。冉老師突然說話瞭:「你怎麼這麼大膽?」
我喘著氣顫抖著說:「我想要你。」
冉老師一本正經狠狠地說:「你再這樣,我就要叫瞭,你是學生呢,怎麼可以這樣對老師?」
我急得都快哭瞭,央求著她:「冉老師,你別叫,我知道我錯瞭,你這麼漂亮,我忍不住。」
她不置可否地把頭歪在一邊,我說:「你就給我一次吧,就一次,我被開除瞭,我發誓從你眼前消失,再也不讓你看見。」
她回過頭來看著我:「你還是第一次吧?」
我及時地紅瞭臉說:「恩。」
冉老師眼裡發出異樣的光芒,聲音變得柔和起來:「那我們快點,等下王老師要下課瞭,撞見瞭不好。」
我從第一眼看見這個女人,就知道她是個騷貨。我把她推著我的雙手拿開,放到頭頂上。我的手像條蛇,沿著她的大腿鉆進去瞭,摸到瞭那裡濕淋淋的一片,我說:「冉老師,都濕瞭呀!」
她閉著眼哼瞭一聲說:「那是生理反應。」
我把她的裙擺撈起來,兩條白生生的大腿掉在床沿,我吞瞭口水,她的腿不像敏的那麼修長,不過比敏的要豐腴,鼓鼓的滿是肉。
我的兩隻手抓住米黃色內褲的邊沿,我要把她扯下來,她閉著眼沒看我,把那渾圓的臀部稍稍抬高瞭一點,脫下來的內褲已經被那愛水浸濕瞭一大片。
這是個成熟女孩的陰道,和敏的完全不同,黑烏烏的雜草叢,蓋住瞭那鼓蓬蓬的山丘,肉縫的顏色不再是敏的那種粉紅色,而是暗紅色,陰唇的形狀也大不相同,長長的兩片黑紅色的肉瓣伸在外面,像她的唇,更像蝴蝶的兩隻翅膀,縫中已是光亮一片。
她抬起頭來看我在盯著那東西看,著急地說:「你快幹我,我們隻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啊?」
她一語點醒夢中人,我趕緊把自己身上的扒下來,放在椅子上。
直撅撅的長甩甩的東西張頭怒腦,靜脈曲張,她也把裙子乳罩解瞭,看瞭我那裡一眼,尖叫起來:「呀,那麼大呀!真看不出來,小小年紀就有這麼一個好東西。你可要輕點幹啊?」
她軟得如一根面條似的倒下瞭,分開雙腿,那暗紅的口子張裂開來,像一頭小獸的嘴。她顫聲說:「你快進來吧!我等不及瞭!」
我站在床沿,把這粗壯的樹根直抵抵地對準口子直塞進去,倒也不甚費力。
她呻吟著「啊」地一聲叫瞭出來,樹根已經全根沒入,肥厚的溫熱的肉蕾將我包裹住,不像敏的那麼緊,反而有一種寬厚包容的感覺,剛剛好。
我開始抽動起來,冉老師便扭動著身子,哼哼嘰嘰地呻吟起來,屁股一聳一聳地湊上來,胸前兩個雪白的奶子也隨著前後波動,她的奶子很是奇怪,不像小寡婦的渾圓,也不像敏的堅挺,像一個饅頭的頂部被過分地拉長瞭,乳頭特別大。
我緩慢地來回抽送,左右研磨,兩片蝴蝶的翅膀在緩緩飛舞,翻動出內裡粉紅色的肉褶,帶出瞭咕咕的流水,發出響亮的「劈劈啪啪」的聲響。
冉老師臉色潮紅,鼻翼微張,她索性把手放到胸前來自己揉搓著,兩條蓮藕似的玉腿攀上瞭我的雙肩,又滑落下去,我還是希望它們在我的肩上,伸手去拾起來,放在肩上用手抱住。
我越抽越快,越抽越快,她的叫聲越來越大,越來越急促。前前後後都抽七八百下自己還沒有泄,我暗地裡感到吃驚。
她的臀部雪白滾圓,猶如棉花團一樣柔軟而有彈性,我一時意亂神迷,劇烈沖撞起來,像咱傢那頭擰≠在草場裡亂沖亂撞,任冉老師如孤舟般在下著暴雨的海面上翻滾,掙紮。
不大一會兒,隻見她繃直瞭身子,拼命地抓著自己的乳頭,脖子向後伸直著,脖頸上的青筋凸顯出來,緊蹙著眉叫道:「我來啦!我來瞭!我不行瞭……啊!」
兩隻眼睛翻著白眼,嘴唇也不停地抽搐,憑空裡一聲驚叫,夾緊雙胯,雙手死死地抓住床單,抖個不停。我感覺自己自己那裡像被跳躍著纏繞瞭。
我醉眼看她如蟲一樣跌動,嘴唇抽搐,雙目翻白,猛地一聲驚叫,雙手死死抓住床單抖個不停,一股熱流湧動著噴流出來,我感到自己那裡像被一隻暖暖濕濕的手緊緊地攥著,趕緊抽身退瞭出來,轉身一瀉如註,射在瞭地板上。
冉老師好大一會兒才喘過氣來,嬌嗔地說:「還跟我說是第一次,你騙人哩!」我紅瞭臉說:「我就隻做過四次嘛!」
她不相信地說:「真的?我好久沒這樣爽過瞭,真爽!」
停瞭一停,她有點遺憾地接著說:「可惜你就要走瞭,這麼帥這麼結實的一個小夥子,要不你來我們班吧。我可以幫你說說。」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我實在是不想再聽這個瞭,我還是對她說:「謝謝你啦!我自己會有辦法的。」鬼知道我有什麼辦法呢。
她偏著臉問我:「你真的再也不見我瞭。」
我說:「你說不見就不見唄。」
她一邊拿紙巾擦著那裡一邊笑瞭:「你還真的較真啊?我要你幹我的時候找不到你呢,你真棒!」
我說:「我也想幹你啊。我又不離開這裡,我想日你的時候可以過來嗎?」
她說:「好啊,我就住王老師隔壁,挨著左手邊第一間就是我的小窩,你要隨時來哦。」
我說:「恩。」
我剛剛把我那裡打理乾凈,下課鈴就響起來瞭,我趕緊抓起衣服飛快地穿起來,冉老師也忙成一團,把裙子往頭上就套,反瞭都不知道,她哈哈的大笑起來,我顧不得那麼多瞭,飛快地穿著衣服……
她塞過來一張紙:「諾,這個是我的課表。」
我隨手一抓塞在口袋裡,飛奔著下樓去瞭。
到瞭一樓,遠遠地看見王老師抱著書本嫋嫋婷婷地走過來,我裝作沒看見她,轉身想從後門就出去瞭,卻被她遠遠地叫住瞭:「向非,這麼快就走瞭啊!」
我隻好停下來立定,等她走過來,我說:「我改天來嘛!」
她有點難過,她說:「不管在哪裡,要好好的努力,記得常常回來看我,我的課表安排你知道的吧。」
我用力地點著頭,我再次感覺那不爭氣的眼淚就快溢出眼眶瞭,怕她瞧見,趕忙轉身走出後門去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