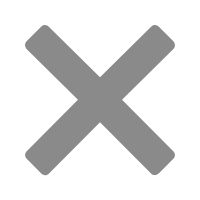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六章 獵槍和兔子
我又聽到瞭她嘴裡冒出這個粗魯的「日」字,剛開始我還很討厭她說這個粗鄙的字眼,聽多瞭也就習慣瞭,而且從她嘴裡說出來,仿佛帶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魔力,像個魔咒那樣能催發欲望的蛇。那條蛇聽到這句咒語,蠢蠢欲動地蘇醒過來,慢慢地慢慢地伸展著身子,終於直撅撅地挺長瞭身子,隔著我的內褲,隔著我的褲子,清晰地抵在她雙胯間的鼓蓬蓬的肉團上。
她似乎也感覺到瞭這條頑強的蛇的蘇醒,她四下張望瞭一下,問我:「什麼在動?」
我有點難為情地說:「還能有誰,你的蘑菇唄!」她好像聽不懂這是個比喻,迷惑地問我:「我的蘑菇?」
我無奈地說:「你不說過她像蘑菇嗎?噢,它更像一把獵槍。」
她尖叫著松開手臂,要從我的身上跳下來。我雙臂緊摟著她的脖子,阻止瞭她這麼做,我想吻她的唇。她呢,哆嗦著說:「槍?為什麼是槍而不是別的?」
我辯解著說:「它看見瞭兔子,它就會動起來?」
她更加茫然瞭:「兔子?在哪裡?」
我幾乎笑得喘不過氣來,我把手順著她的大腿,在她的短裙裡面繞過她的臀部,從後面彎曲瞭指頭戳瞭她那裡一下,告訴她:「兔子在這裡!」
我的笨女孩終於領悟瞭這個比方,尖叫起來:「呀,這才多久呀?你又要日,都會被你日腫瞭呀!」
我試探著問她:「你現在不想要?」
她把頭埋在我的胸膛裡,嘟嚨著:「噢,這倒不是,你都不愛惜一下自己的身體,我當然巴不得你時時刻刻日著那裡呢!」
我放心瞭,也放肆起來,直截瞭當地請求她:「那……我們開始打獵吧?」
她嚶聲說:「就這樣?你在下面?」
我覺得這應該是可以的,就說:「恩,就這樣,你在上面,試試吧,如果不行,你再到下面來不遲。」
她說:「你可真會開玩笑,還獵槍還兔子呢!真不害臊。」
我抬起她的下巴,誠懇地說:「別害怕,我的兔子。我愛你。」
她學著我的聲調,聽起來怪怪的:「我不怕,我的獵槍。我愛你。」
我不喜歡她這樣學我說話的聲調和節奏,故意沉著臉說:「現在開始吻我吧,我要吻。」
她撥開我抬著她下巴的手指,俯下身來緊緊抱起我頭,我不得不支起上半身來。她的嘴唇滿臉滿鼻子狂熱地舔吻著,尋找著我的嘴唇,接著她找到瞭。她把嘴唇輕輕地送到送到我的嘴上,她的唇微微開啟,流轉而出讓人心醉的氣味,像淡淡的玉蘭花的香味。
我啞著嗓子從喉嚨裡發出聲響,像隻狗那樣乞求她:「把舌頭給我。」
香軟柔滑的舌頭像蛇信子那般吐瞭出來,越過她的牙齒,越過我的牙齒,找到瞭另一條熟悉的蛇,兩條蛇纏在一起撥動、翻滾。
我試圖尋找甘甜芳香的源頭,我要找到它們的所在,而她臉上背上的熱氣把我包圍起來,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朦朧,我什麼也不知道瞭,她把全身力量都用在我的唇上,緊緊地抱著我的頭,她的唇嚴密,柔軟,滑膩,帶著熱烈得發燙的涼爽,往下按著;我的唇,貪婪,熱烈,有力,往上湊合,仿佛兩個人要化合成一個人。
她不安地蠕動著屁股,扭動著腰肢,那熱乎乎鼓蓬蓬的兔子放肆地抵在壓迫著堅硬的獵槍的槍口,有意無意逗弄試探著獵槍的溫度。
我的血液像燒開的熱水沸騰起來,我的指尖慢慢往下移動,急切地在兩人壓迫著的身體之間尋找著,固執地推進。
她把身子微微抬起來放縱瞭它,我的中指觸著瞭潮濕柔軟的進口,終於到達瞭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她觸電般地顫抖瞭一下,驚叫瞭一聲。
我的手指就像一條小魚,遊弋在她如水的身體之中。滑膩的液體滲透瞭出來,她扭動屁股拼命掙紮,她終於抬起頭,不再吻我瞭,半瞇著雙眼,半開著嘴唇,發出攝人心魄的動人的吟哦聲。
她的臀部向下退去,我的手指從中滑落出來,魚兒帶著濕漉漉的身體離開瞭它的水。她直起身來,坐在我的小腿骨上,把我的皮帶解開,把我的拉鏈拉開,把褲子和內褲一並拉到膝蓋處。
晚風和著月光吹在我的大腿上,帶來絲絲微微的涼意。那不是一把獵槍,那是一尊打炮,昂揚大氣,直指天穹,威風凜凜。她柔嫩的手指纏繞上來,把那最後的柔軟的屏障剝離。
她輕輕咽著口水,喉嚨裡發出「咕咕」的清響,夢囈般地說:「我喜歡它,好大噢!」
我的嗓子眼裡像許多蟲子在爬行,癢得人難受,癢得人燥熱難耐,我的手無措的攤開在身下的苜蓿上,無助地抓緊苜蓿的根。她低著頭細細地,驚惶而胡亂地把玩著它,愛不釋手,我知道她隻是想再一次看清楚它,眼睛裡滿是純凈的光亮,不帶一點邪念。那獵槍的槍口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我哼著說:「不是那樣!」
她回答說:「要怎樣?」
我說:「輕點,上下套弄。」我撥開她的手指,做瞭個示范。
她的手溫柔地活動起來,輕盈得如同一隻蝴蝶,在花叢中扇動著美麗的翅膀,上下翻飛。我閉上眼睛,看見瞭我的身體像一葉輕舟,在濃的化不開的陽光下,在蔚藍的海面上,隨著起伏的波浪蕩漾。
我感覺得到她胸前那對圓圓的、隆起的、堅實的乳房在顫抖。我體內的火山在醞釀在燃燒,冒著「噝噝」的熱氣。我的身體像是米粥一樣,在鍋裡的混混沌沌地沸騰起來。不知道為什麼,我更偏愛她的那裡包覆著,而不是她的手,總覺得缺少瞭什麼。
我問她:「你那裡怎麼樣瞭?」
她如此沉迷於玩弄獵槍,仿佛如夢初醒地說:「早濕瞭,仿佛有螞蟻在裡面爬。」
我噓瞭一口氣說:「來吧,兔子!我可愛的小兔子!」
她直起身來,要脫掉內褲,我打著手勢制止瞭她:「別脫,脫衣服就好瞭啦。」
她就把短裙從頭上取下來,扔在我的腳跟上。她再也沒有昨日的羞羞怯怯,笨拙地坐上來,我伸手把她的內褲扒在一邊,讓那鼓蓬蓬的饅頭暴露出來。
她低頭看著那濕潤的洞穴,用手把內褲再往邊上理瞭理,用手拉住。我扶扶著獵槍,對準瞭我可愛的兔子。
她慢慢坐瞭上來,獵槍準確地命中兔子瞭,或者說兔子準確地撞到瞭獵槍的槍口上,她閉著眼仰起頭來把秀發甩在後邊,嘴裡拖著長長的滿足的調:「噢……」緊閉瞭雙眼,仿佛完全陶醉在被充滿的快感中。
我握住她的白玉似的大腿,試圖努力抽動,可是被她直立著的身子壓得死死地,動彈不得。軟軟濕濕溫溫的肉蕾緊緊地包覆著,我迫不及待地向她湧動,我急切地說:「我動不瞭,你動一動呀!」
她生疏地扭動腰部,動作那麼慢,不過還好,這樣好多瞭。她仿佛第一次駕著小木船出海,生怕翻船瞭似的,那麼小心翼翼地搖著櫓。小兔子中槍後卻不安分,撲撲地緊縮抽搐,報復似的撕咬著發燙的槍管,它已生命垂危,就要死去,卻不甘心地掙紮,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回光返照。
我幾乎是在哀求她:「親,快點搖,再快點啊!」
她快快地搖瞭幾下,感覺也沒什麼大礙,才放心大膽地搖動起來,我的女人終於擺動起來,快樂地唱起歌來,快感如同海浪沖擊拍打著堤岸,她的呻吟的歌聲,分不清是痛苦還是沉迷。
月光流瀉在她的發上,流過她玉脂般的背脊,使她的輪廓邊緣發散著一圈亮亮的光暈,月亮給我的女人披上瞭銀色的外衣瞭。此刻我的女人,像是開足瞭馬力拖拉機,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酣暢淋漓地顛簸著。她胸前的雪白的肉團歡快的蹦著,挺起或下落,秀發在月光的微風中輕舞飛揚。
我的女人突然輕聲叫道:「我不行瞭!」我知道她是想和她的男人一起高潮。
她緊接著挺起上身,緊緊地夾緊胯骨,伸直瞭脖頸,臉使勁地向後伸向天空,大聲朝著月亮叫喊:「快來呀……快點啊!」
叫喚聲猶如困獸落入陷阱時絕望的慘叫,穴內所有的黏膜緊緊地糾纏住吸附住男人,微微急促的痙攣顫動,我知道她要來瞭,她終於傾瀉瞭出來。
她如同暴風過後被掀翻瞭跟的河邊的垂柳,軟軟的伏倒下來,趴在我的身上喘著粗氣。我把她拉上前來,獵槍在熔爐的滾湯裡,馬上就要走火瞭,子彈「啪啪」地打在兔子後面的圓圓的山峰上,放瞭兔子一條生路。
恢復平靜的田野裡,隻有月光靜靜地流瀉,寂靜得可怕。兩個人疊躺著,胸部緊緊地貼在一起,大汗淋漓的,滑不溜秋的。
月亮慢慢地向天幕的中央移動,我問她:「今晚不回去瞭吧?」
她說:「怎麼可能不回去呢?半夜田裡涼哩。」我知道我的本意不知是這樣問的。
我又說:「你媽媽會等你回傢吧?」
她說:「哎呀……怎麼把這給忘瞭?快快起來,送我回去啦!」她趕忙爬起來找衣服穿上,我哭笑不得,這算什麼事呢?
納悶歸納悶,我還是爬起來瞭,把褲子拉上,把襯衫扣上。
她「噗嗤」笑瞭:「笨蛋,上當瞭吧?也不用腦子想想,如果我媽媽等我,我會跟你在這裡鬼混這麼久?那是找死哩。」
我一頭霧水,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她笑得更歡瞭:「你不願意讓我去你那裡?」
我懵懵地說:「這……求都求不來呢,當然願意啦。」
她解釋說:「我都給燕子打好招呼瞭,她可是我的死黨呢!」
我還是感覺有些不踏實:「怎麼說的呢?」
她說:「這都不會啊,我放學和燕子回瞭我傢的,出門的時候我和媽媽說今晚在燕子傢復習,不回來瞭。媽媽每次都同意的。」
我對她說:「改天也叫燕子一起來吧?」
她警覺地說:「為什麼要她一起來?她會愛上你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我……你是最漂亮的啦。」
她不安地說:「我知道你心裡隻有我,可是我怕別人打你主意啊!」
我很肯定地說:「不會的,我有什麼好的,那麼無趣,那麼枯燥。」
她說:「我就不信瞭,沒有女孩追過你。」
我說:「沒有,我不怎麼註意!」
她調皮地說:「你長得人模狗樣的,那麼挺拔結實,還偽裝得純純的,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錯覺,成績又好。我不信你們班那些女生都瞎瞭眼瞭?」
是有那麼幾個女孩子,下課經常過來搭訕,隻是我笨嘴拙舌的,也覺得沒什麼好說的,總是搭不上話茬子。其中有一個姓張的高二的,我還對她印象蠻好的,清清秀秀的,身材很苗條,瓜子型的臉龐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閃著兩隻明亮的大眼睛。
她有時候來找他哥哥,她哥哥是我們班的,很多次經過我面前的時候,低著頭極輕快地瞟我一眼,然後像隻小鳥快步走掉,估計他哥哥是知道的,他哥哥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好,甚至讓我感到要把我吃掉的企圖。
她見我沒有說話,就問我:「你在想什麼呢?」
我說:「累瞭,我們回去吧,明兒還要上課呢?」
她抬頭看看天上的月亮說:「噢,不過你得背我。」
我背著她穿過田野,進瞭院子,在梨樹的樹影裡把她放下來,繞到後面去看房東睡瞭沒有,房東房間的窗戶一片漆黑,大我就躺倒床上概還沒有回來吧。
我又繞回來,大門一般是不插門栓的,我輕手輕腳地推開大門,一前一後進瞭門,把大門重又輕輕地合上。
上瞭閣樓,她突然憋不住笑瞭:「瞧你那出息,你是在偷別人的老婆麼?這個模樣。」
洗漱完,就躺倒床上動不得瞭,連續做瞭三次,現在才感覺有點胯骨有點酸痛,全身上下就像快散架瞭似的。我迷迷糊糊就要睡去,看著她還坐在床沿不動,我聽見她在床前窸窸窣窣就嘟嚨著叫她:「怎麼啦?還不睡啊?」
她說:「我會認床,第一次和你睡覺,感覺好奇怪的。」
我說:「那好吧,你就不用睡瞭!不過把燈關瞭,我可困死瞭。」
她就把燈關瞭,屋子裡一片漆黑,關瞭燈突然讓我更加清醒瞭,我聽見她在床前窸窸窣窣脫衣服的聲音,緊接著她就轉到被子裡來瞭,我伸手去撥她說:「你不認床瞭?」
她在黑暗中悄悄地回答我:「關瞭燈害怕嘛?」
我說:「到床上就不怕瞭?」
她說:「有你我就不怕瞭呀!」
我說:「睡過來,不要離那麼遠,我要抱著你。」
她很聽話的躺過來瞭,把頭搭在我的臂彎裡,伸手在我臉上輕輕地摸索著我的輪廓,溫軟的軀體蜷曲著緊緊地貼著我。
閣樓上的黑暗濃濃厚厚地,黏稠得化不開似的包圍著我和她。睜開雙眼看那黑暗,原來黑暗也是有顏色的,漂浮著瞬生瞬滅的光線和光球,一層一層地落在我的臉上。
過瞭一會兒許久,房間裡的黑色開始像黑暗的角落慢慢消隱,周圍物什的輪廓漸漸分明起來。敏均勻的呼吸聲在我耳邊響起,嘴裡時不時時傳來含含糊糊地夢囈,被窩裡有一種淡淡的少女的體香散發出來,彌漫在我的四面八方,彌漫瞭整個閣樓。
一陣睡意襲來,我終於進入瞭夢鄉,我做瞭一個很長很長的夢,整個夢隻有一個故事,卻沒有她,在夢裡我到過一些地方,似曾相識,讓我莫名地驚懼,我常常做這樣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