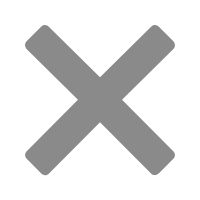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十二章 曙光
我幾乎是跑著回到閣樓上的,敏已經來瞭,床單已經鋪好,正在方桌邊看翻那本《素女經》呢。我咚咚地跑上樓來,她趕緊把書放下瞭,一臉尷尬的樣子,紅得不成樣子。
她訕訕地說:「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沒回答她,我也不想對她說謊,躺床上去瞭,床單香噴噴的,還有洗衣液幸福的芳香。
她見我不回答又問我:「這本破書上的字怪怪的,你看得懂嗎?」
我跟她說我看得懂,我想起瞭爺爺小時候教我看《唐詩三百首》,也是繁體豎排的,每一首後面都附有小註,和現在的註不一樣,基本上都是引用古人的詩句或者經典原句做註,也是那麼的難懂,爺爺便一個字一個字地教我,一句一句地給我解釋。一本書下來,斷斷續續花瞭一年多的時間,所以我認得很多繁體字,也知道古文大概是怎麼斷句的。
敏聽著我說這些,好奇地問我:「你爺爺還在吧?」
我想起爺爺死的時候爸爸像個孩子似的哭瞭,我說:「他死瞭。」那時我還夢見瞭爺爺,跑去跟爸爸說爺爺還沒死,現在想起來那時的我真的純真得讓人想哭,不知人有三苦。
她看見我悶悶不樂地,也就不問瞭。
她神神秘秘地跟我說:「我媽叫你去一起吃飯?」
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
她一字一頓興高采烈地說:「我——媽——叫——你——去——我——傢——吃——飯。」
這像一句驚雷,我愣瞭大半天說不出話來。
她看見我呆瞭,搖瞭搖我:「不會吧?這就把你嚇傻瞭?也太不經嚇瞭吧?」
我定瞭定神問她:「她怎麼知道的?」
她拍瞭拍我的腦袋說:「你這裡是不是有問題瞭?我舅姥爺經常去我傢,我舅姥爺和她說的呀。」
這下更糟瞭,那天早上我們幹得那麼大聲,也不知房東醒瞭沒有,我著急起來:「那我們豈不是完瞭?那天早上你那麼大聲音。」
敏的臉一下刷的紅瞭:「說你傻你還真傻,要是舅姥爺聽到瞭,把這個告訴我媽瞭,我還能完整地站在這裡,還能這麼高興?」我還是覺得心裡沒底,怎麼想怎麼像個鴻門宴,不知道到底去還是不去。
她見我猶猶豫豫的,瞪起瞭眼:「去還是不去,你說個話呀?」我有選擇嗎?
我換上我的白色運動鞋,那是我最好的鞋瞭,平時都舍不得穿的,忐忑不安地往她傢去瞭。一路上我腦袋裡像炸開瞭鍋,亂亂糟糟的。我不停地想像她媽會是什麼樣子的,會說什麼話,我該怎麼回答。在路上她非要我牽著她的手,可是我怎麼也輕松不起來。
她緊緊地攥住我的手掌,手心都攥出水來瞭,看來她也不輕松嘛,還說我。一路上都沒什麼話,我心裡七上八下的,如臨大敵。她堅持要我走前面,這讓我壓力更重瞭。
她傢就在街邊,開瞭個小百貨店。遠遠看見她媽媽坐在店門口的藤椅上,短發別在耳根後面,手裡拿個雞毛撣子,肩上挎個黑色的小包放在面前,莊嚴地坐在店門口。
她撒開瞭我的手,像隻小鳥向她媽媽飛奔過去,抱著她媽媽又是親又是叫,好像分別瞭很多年似的。
等我走到跟前,她才松開瞭她媽媽,跑到她媽媽後面去瞭。她媽媽被她弄得氣喘籲籲,好不容易解脫出來,臉上的笑還沒有松懈下來,理瞭理被敏弄亂的發鬢,回頭問敏:「這就是老學校的那個向非?」
敏趕緊點點頭,我趕緊說:「阿姨,你好!」
還好,我還以為她看著那麼嚴肅,原來說起話來滿臉堆笑,是那麼的慈祥,可以在敏身上看到遺傳瞭媽媽的某些內容。
看起來阿姨快五十歲瞭,眼角已經爬上瞭淺淺的魚尾紋,也許是長年的辛勞讓她過早地衰老瞭。不過短發濃密油亮,隻有稀稀疏疏的幾絲白發。眼睛是漂亮的雙眼皮,秀氣而淡定,明亮而不渾濁。那高高的鼻梁和抿著的厚厚的嘴唇,顯示出不衰的活力。身材勻稱,顯得有點微微地胖,不說話的時候,臉上掛著精明的略帶譏嘲的表情。
她點點頭,回頭對敏說:「不錯呀,很有禮貌的一個小夥子。」
敏做瞭個鬼臉,對著她吐瞭吐舌頭,她伸手想給敏一巴掌,敏跳開瞭。
她惡狠狠地說:「鬼丫頭,還不進去把菜熱瞭?」轉過頭來,重又堆上笑容對我招招手:「去吧,你們先進去,我馬上就進來。」
敏在後面對我做瞭一個勝利的「V」形手勢,跑過來拉著我穿過店鋪,從店鋪的後門進去瞭。
這個院子有點像以前那個時代的四合院,不過瓦房變成瞭平房,墻上貼著潔白的瓷磚,都是她一傢人住著,她有三個哥哥,有兩個已經成傢立業分傢出去瞭,最小的哥哥去市裡讀高中瞭,聽說是市裡最好的中學。
進瞭堂屋(堂屋相當於我們說的客廳,隻是和客廳不同的是,裡面對門的中央掛著天地諸神祖宗的排位,俗稱「傢神」,逢年過節這裡就是祭拜祖宗的祠堂,平日裡也有當做起居室招待客人的,界限不是很分明。)她並沒有立即就去熱菜,而是帶我去參觀她的閨房:房間收拾得乾乾凈凈的,一張淡青色的席夢思床,床柱上掛著潔白如雪的蚊帳,床上面鋪著粉紅色的被褥。
床面前的窗前放著一張寫字桌,書本,文具整整齊齊地放在上面,桌面一塵不染,白色蕾絲點綴的窗簾,拉開能看到窗外一片已經收割瞭的稻田,隻有光禿禿的短短的稻樁杵在田裡;整個房間有著熟悉的芳香的味道,淡淡的梔子花的味道。
敏像一個小孩炫耀玩具一樣炫耀她的閨房,臉上掛著幸福的滿足的笑仰著躺在床上打滾。我在老傢是閣樓,在這裡還是閣樓,傢裡的閣樓還沒有這裡的閣樓好,一到冬天四面來風,躺在被子裡瑟瑟發抖。
阿姨的聲音從客廳裡傳進來:「鬼丫頭,叫你把菜熱熱,熱瞭嗎?」
敏觸瞭電一樣從床上彈起來,飛快地沖出去,我也跟在後面出來瞭。
阿姨一邊滿屋子用雞毛撣子追著她,一邊生氣地大喊大叫:「就知道玩,就知道玩……」敏咯咯地笑著跑著,跑到我背後拉著我的衣擺,尋求我的庇護。
阿姨揚起雞毛撣子打不到她,氣呼呼地住手瞭:「這孩子,一天瘋瘋癲癲的。」
吃飯的時候,敏又變回瞭楚楚依人的小鳥,坐在媽媽身邊,邊吃邊瞄著我,阿姨歉意地說:「都是些傢常菜,自傢地裡出的,都沒什麼招待你的,怪不好意思的呵!」
不好意思的是我,我說:「阿姨,真的挺香的,我第一次吃這麼好吃的菜。」
阿姨笑瞭,看看女兒說:「不是說向非很木訥很老實嗎?我看不像呀,這麼會說話,怪不得喲……」
敏紅著臉低著頭,阿姨向我的父母問瞭好,我問她:「叔叔呢?怎麼不一起吃飯?」
阿姨說:「還不是為瞭那爛攤子東奔西跑的,今天進貨去瞭,晚上才回得來哩。」
她又問到我在老學校的一些情況,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說,就實話告訴瞭她:「我被勸退瞭。」
阿姨驚訝的看著敏,又看看我說:「怎麼沒聽她提起過呢,這麼大事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就把那天的批鬥大會跟她大概說瞭一遍,敏也驚訝地看著我,我無法預見他們的反應,突然間我感覺的我是個陌生人,跟她們的距離那麼遙遠。
阿姨聽完瞭,哈哈大笑著誇張地鼓起掌來:「這算什麼事呢?就該那樣說,老學校每天都要這樣發動學生修這修那的,不就是為瞭省那幾個臭錢麼?」
從來沒人說我做得對,隻有她這樣說,這樣我又確定她是自己人瞭。
她看著我默不作聲,悶悶不樂的樣子又說:「這是你爸爸媽媽知道麼?」
我說:「我還沒告訴他們,怕他們擔心哩!」
我把傢裡的情況大約跟她說瞭一遍,阿姨一拍胸脯,打著包票說:「孩子你別愁,多大點事兒哩?包阿姨身上瞭,又不是隻有它一個學校,新老學校的老師很多都是我們的熟人,你愛去哪個學校你說,,隻要你開口,說去哪就去哪?」
阿姨的話讓我喜出望外,她說話是如此的斬釘截鐵,讓人信任和欣慰。原來這就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我感激地對她說:「老學校我是不想回去瞭,我想去新學校,跟敏一個班。」
阿姨真的夠義氣,像個哥們兒那樣:「好,就這麼說定瞭。你們的事我也聽敏的舅姥爺說過瞭,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我作為傢長,我有話要說。」
敏和我都不吃飯瞭,緊張的等待她的發落,我們也不知道房東究竟說瞭什麼,阿姨停頓瞭好一會,我們的心揪得緊緊地,她終於語重心長地說出來下面的話:「說嚴重點的話,你們都還沒成年,這算早戀,可是我們也是過來人,所謂『不是冤傢不聚頭』,誰喜歡誰這都沒錯,時代變瞭,不像那年月偷偷摸摸地喜歡,不敢說出口,如果不是她舅姥爺跟我說,你們打算瞞我一輩子?」
我和敏面面相覷,大氣也不敢出,心裡咚咚直跳,她停瞭停接著說:「我現在知道瞭,我也不批評你們,作為傢長,我給你們提一些建議是應該的吧?」
我和敏一個勁地點頭,她說:「一切以學習為重,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共同進步,現在是學習的時候,錯過瞭這個時光就再也找不回來瞭,那可是終身的遺憾哩,我這孩子,一天就是頑皮,不像她小哥那樣認真,你看起來穩重,你得隨時說說她,收收她的心。」
我說我會的,她又說:「你們那天早上的事,她舅姥爺也說瞭,我當時氣不打一處來,想打死她,但是回頭想想,不發生也發生瞭,就算我把她打死瞭有用什麼用呢?到現在我還沒告訴她爸爸哩。今天有這個機會,把你叫來主要也是說這個事,你們還年輕,承擔不起這個責任,但是愛美之心每個人都有,隻是你們的路還長著,要懂得保護對方,小非,你知道我說的這意思吧?」
我趕緊使勁地點點頭,她轉頭看瞭看敏,敏臉紅得像熟透瞭的蘋果,在那裡揉搓著雙手。
阿姨看我們緊張得不行,嘆瞭口氣說:「這孩子還騙我說是去小燕傢做作業,以後你們也不要偷偷摸摸的,隻要你們聽我的話,好好學習,在期末的時候給我拿個好成績出來,她爸爸那裡,我知道怎麼辦的,當年我們還不是早早地就把那事做瞭,現在還不是走在一起瞭,雖然辛苦,日子還是過得去的。」
說完後站起身到電話機旁撥瞭一個電話,她在給敏的班主任打電話,把我的情況在電話裡說瞭一遍,回過頭來說:「行瞭,明天就去上課吧,給你們加瞭一張新課桌。」
敏吐吐舌頭給老媽豎起瞭一個大拇指。告別的時候,阿姨叮囑我說:「你和小敏經常回來吃晚飯,什麼都是現成的,外面有什麼好吃的?你們做的東西能吃嗎?」
到瞭街上,我們興奮得都快飛起來瞭,我背著敏從街頭一直跑到街尾,她張開雙臂,輕盈得像陣風。
陰霾終於散去,太陽就要出來瞭,這一天是十月十號,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從今天開始,我們不用怕別人看見,不用怕別人說我們早戀;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囂張,可以牽著手去天地的任何角落;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瘋狂地做愛,放肆地呻吟;從今天開始,我看到全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