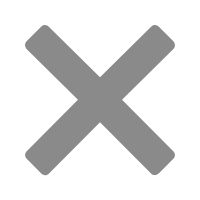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十四章 喇叭的隱憂
早上我起得很早,天剛蒙蒙亮我就起來瞭,敏還在甜甜地熟睡,像個嬰兒那般純真的臉蛋讓我不忍打擾她。
我下樓洗漱完畢,拿起英語課本到前面的小路上借著晨光朗誦,,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不過我常常在院子裡做這早課,今天是因爲敏還在熟睡,怕吵醒她,所以就走遠一點。
看看上課的時間到瞭,我才回去。敏已經起來瞭,書包都給我準備好瞭,正在焦急地等著我回來,有人等待的感覺真是幸福。
我們在校門口買瞭早點,手牽著手走進瞭校園,這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新學校的學校也是新的,唯一讓我不安的是空氣中彌漫的敵意,這從我們經過操場的時候教學樓上發出的哄叫聲和唿哨聲可見一斑。
在這裡我是一個入侵者,而且犯瞭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奪走瞭他們日思夜想苦苦暗戀的校花而沒有通知他們,這讓他們莫名地絕望,甚至於爆發憤怒。在我們手牽著手走進教室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強烈瞭,我享受這種敵視,就像敏的媽媽說的那樣,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新課桌,比誰的都新,甚至比講臺那張桌子還要幹凈。
我不需要用一場考試來證明自己,當班主任向同學們介紹我的時候,大傢都沸騰瞭,不錯,我就是那個向非,在期中會考中力壓新老學校的向非,而我現在就和他們在一起,將和他們一起對抗我的驅逐者們。
我是個狂妄的人,但是我並沒有表現出來,我知道那樣做的危險,我隻是站起來向我的新同學們欠欠身,企求博得他們的好感。如果有可能,我還會盡量幫助他們,比老師還熱心,後來的日子證明這一切是那麼的徒勞,他們不過是草民,我的命運不在他們手裡。
課間操的時候,老學校那高亢的喇叭在宣佈發獎,聲音清晰可聞,原本新老學校就隻隔著半公裡不到的路程。這天雖然對我來說是個新的開始,但是也是個奇怪的一天。他們在給我發獎,在給一個被他們驅逐在外的學生頒發獎狀,給一個不存在的對象頒發獎狀,這說起來有多可笑?
「初三級語文會考第一名:向非,請上臺領獎。」
沉默瞭好一陣,喇叭聲又響起來:「請上臺領獎……」
看來他們是知道我不在老學校瞭,可是還是繼續往下念,聲音越來越洪亮:「初三級數學會考第一名:向非,請上臺領獎……」
這聲音讓我感到不安,足足讓我聽瞭整個課間操的時間。
敏就在我旁邊,她說我臉色變瞭。是啊,這讓人太奇怪瞭,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想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班主任挾天子以令諸侯,把驅逐我這件事給蒙住瞭,教務處的成員一無所知,這種可能性非常小。一種是他們在第一時間知道瞭我轉學到新學校的消息,這隻是播給新學校聽的,這是個反間計,這個可能性非常大。
果然在早操解散瞭之後,新班主任就找到瞭我,問我是不是下決心在新學校堅持待到最後,這讓我很是慌張,我把我被驅逐的前前後後跟他說瞭一遍,他好不容易才相信瞭我,這讓我的心稍稍安定下來。上課的時候我依然神不守舍,我很清楚這隻是開始,故事不會這樣終結。
欣慰的是,一天的時間,我就跟班上的同學熟絡起來,他們總喜歡拿些古怪的題目來刁難我,而我都給瞭他們滿意的回答,這讓他們驚奇不已,因爲他們帶來的題目很多都是奧賽上的題目。
這裡的老師很年輕很熱情,雖然課上的不是那麼好,可是很細心,這在老學校是見不到的,老學校的老師都是有資格的老教師,他們骨子裡就是傲慢的,不可一世的,在他們眼裡:「學生一無所知,而老師則無所不知」。
今天還算差強人意,隻是放學的時候發生瞭一個小小的插曲:我和敏牽著手走出校園的的時候,有個瘦弱的流裡流氣的小混混公然對敏進行肆無忌憚的調戲,說著粗俗不堪的話,視我爲無物。他罵敏是「騷母狗」,還問我是不是日爽瞭,我二話不說就想沖過去給他一頓,敏死死的拉住我,叫我不要惹事,說他們是什麼「雙龍幫」的。
去他媽的「雙龍幫」,我還是揪住他的衣領給瞭他幾個耳光,打得我手都痛瞭,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他像「臟臟」那樣叫著「你等著,有你好看的」,哭著跑開瞭,很多放學的孩子在圍觀,有的說打得好,是該教訓教訓這種人渣瞭,有的說這回有好戲看瞭,說我完瞭。
「雙龍幫」我聽說過,我們老學校也有他們的成員,他們老大是新學校初二的任雙龍,因而得名「雙龍幫」。這人年紀不大,做事下得瞭手,兇狠毒辣,他們一直橫行於新老學校,據說有個惹瞭他們的在道上混的被他們剁掉瞭一個手指,還有人說某某女生被任雙龍強奸瞭之後忍氣吞聲,不敢聲張。今天我做瞭這事,他們肯定不放過我。
我把這種擔心告訴瞭敏,敏也不知所措,隻是叫我隨時提防著點。我叫敏暫時回傢避避,這幫瘋狗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張牙舞爪地出現在「狀元樓」。敏說什麼也不走,我發起火來大聲地呵斥她,她才不情願的地去找她媽媽瞭。
回到傢,我就去廚房裡把我從傢裡帶來的砍柴刀拿出來,在梨樹下的石頭上磨得錚錚發亮,陽光下亮晃晃的刀刃如此刺眼,我本來是用它來削土豆皮的,隻是我確實沒什麼防身的武器,拿來充數罷瞭。
雖說是一把砍柴刀,卻非一般的西瓜刀可比,完全是黑色的精鋼鍛造,近一尺來長,刀把和刀身一體鑄造,光刀背就有半公分厚,拿在手裡沉沉地墜手,小時候我經常提著它和爸爸到松樹林裡去砍柴,,聽爸爸說這把刀爺爺年輕時候就在使用瞭,是村裡赫赫有名的王鐵匠親手打造的,這讓我覺得有點哭笑不得,這麼有來歷的刀居然被我拿去對付沒有來歷的小人渣。
對不住瞭,爺爺!從今天開始,我就得帶著它瞭。我把房東放在窗臺上晾曬的牛皮割下來,綁紮在冰冷的刀柄上,好讓我舞動的時候不至於脫手。
說實話,赤手空拳一對一我誰也不懼,我就不信任雙龍比我傢那擰≠子還猛,就算勇猛如擰≠子,我常常在草場裡追上它,抱著它的脖子把它扭翻在地。不過我的反應似乎有點過激瞭,一夜相安無事,隻是把敏叫回傢去瞭,顯得有點寂寞難耐。
我復習瞭今天老師安排的功課,把明天要讀的書放到書包裡,找來一塊紅領巾把刀身包住,塞到書包的夾層裡拉上拉鏈,雖然今天無事,可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啊,那些都是瘋狗。一切準備妥當,我就上床睡覺瞭。
到半夜的時候,我迷迷糊糊聽到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叫我:「向非,向非。」我以爲又做噩夢瞭,趕緊爬起來把燈拉亮,四下裡張望,原來那聲音是從堂屋傳上來的。我的第一反應是:是不是敏半夜熬不住,跑這裡來瞭。可是這又不像敏的聲音,敏的聲音柔婉嬌媚,而這聲音沙啞疲憊,仿佛熬瞭很長的夜似的。
正思量著,小寡婦的頭在樓梯上探出來說:「向非,你醒啦呀,幫幫我吧,房間的燈壞瞭。」
我叫她下去等著我,我穿上衣服拿著手電筒下樓來。她正在堂屋裡直打圈,我和小寡婦都沒說過話,隻是見面點點頭而已,不過俗話說:「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房東的面子上,這忙我得幫。
我問她:「房東呢?」
她恨聲說:「老不死的還在打麻將呢,今晚輸瞭兩千多,他要翻本,我等不瞭他先回來瞭,誰知這燈怎麼也拉不亮。」
進瞭房間,小寡婦去端瞭張凳子墊著,幫我打著手電筒,我把燈泡下下來,用手電筒照著看瞭看。
我無奈地對她說:「這個沒法瞭,鎢絲都壞瞭,有現成的備用燈泡就可以換瞭。」
她跺著腳說:「這可哪裡去找啊?我都不知老不死的放哪裡的。」
我想瞭想說:「要不我把我樓上的那個下下來吧,安在你房間裡先用著。」
她搖著頭說:「那怎麼成呢?你沒有瞭,怎麼睡呢?」
我呵呵地笑瞭:「成,睡覺還用燈嗎?我又不怕黑。」
我跑上閣樓去把燈泡下瞭下來,給她裝上,小寡婦感激地說:「你真好!」我不好意思尷尬地笑瞭。
她見我紅瞭臉,頓瞭頓又問:「你女朋友呢?在樓上睡著的吧。」
我訕訕地說:「她今晚沒來哩。」
一時間都找不到話說,我正準備上樓去瞭,小寡婦突然低低地說話瞭:「你能陪陪我嗎?我一個人怕。」這就句話讓我怔怔地定住瞭,心裡砰砰直跳騰。
小寡婦低著頭紅瞭臉不安地拉著衣角,咬著嘴唇。看她欲語還休的模樣,我知道這個婦人是不是想來瞭,她真是想幹想瘋瞭。
我說:「房東要回來呢,你不怕他看見。」
她擡起頭急切地說:「他不回來瞭,兩千塊夠他翻到早上,還要手氣好。」
我還是有點不放心,就說:「這樣還是不好吧?」
小寡婦笑瞭:「你想多瞭,我隻是害怕,讓你跟我說說話而已。我們又不做什麼的,再說啦,你看得上我們這種女人?」
這回輪到我不好意思瞭,我說:「要不我們到閣樓上去吧,那樣好些。」
小寡婦使勁地點點頭,她今天還是穿那一襲碎花輕薄裙子,隻不過裡面加瞭內衣,手上戴瞭手套,還是一樣的嫵媚。她也許是知道的,今天的向非並不是那個不諳人事的少年,而是一頭兇猛的野獸瞭,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和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躺在一張床上,不止是說說話而已。
我把燈泡換上來裝上,反正下面也用不著。我脫瞭衣服鉆進被子,她卻坐在床沿不說話,低頭看著地板,腳掌不住地蹭著地板,有點焦灼不安。
我還不知道怎麼稱呼她呢,就問她:「我該叫你什麼?」她還是低著頭柔柔地說:「楊雪,雪花的雪。按輩分你得叫我奶奶。」
怎麼能這樣叫呢,我很不情願地說:「你那麼年輕,叫你奶奶,把你叫老瞭,不好,我還是叫你雪阿姨吧?」
她急切地說:「不要,你可以叫我雪姐。」
我叫瞭她一聲:「雪姐。」她咯咯地笑瞭。
我從被子裡直起身子,伸出手撫摸她海藻般的長發,找到她雪白的脖頸,滑過去挽住她的脖子,她沒有過多地掙紮,我就把她拉倒在床上瞭。
她蹬掉高跟鞋躺上來,背對著我說:「我們說好的,你隻陪我聊天的,不做的。」我說恩。
我心裡像小鹿一樣撞的很厲害。我也不敢輕舉妄動,我們一直在說話,她說她的初戀,說她的小孩,說她的人生,有歡喜也有抱怨,我靜靜地聽著,不時地插上幾句話。
她突然轉換瞭話題說:「小敏真騷,那麼大聲響,那天早上我被吵醒瞭,字字聽得分明哩。老不死的也醒瞭,聽得我心窩子上像有螞蟻子在爬動,伸手去摸老不死的那裡,軟趴趴的像條死蛇,還是你們年輕人好啊!」
我說:「你還不是騷,隔三差五地就叫,我都聽見瞭。」
她嘆瞭口氣說:「唉,你們到瞭我這年紀就知道瞭,想要的時候裡面癢得炸開瞭來,老不死的好不容易硬梆起來,幾下又不行瞭,就隻會掏掏摸摸哩,哪裡得到他一時半會兒的實在?」
我好奇地說:「你不是有個大大的那個麼?」
她忽地轉個身來:「你看到瞭,你是怎麼看到的?」
我知道我說溜瞭嘴,我把她身子撥轉,直接把她按住。她像隻被抓住瞭的兔子一直掙紮,說不知道我是這樣的人,早知道她就不上來瞭。
人都到床上來瞭,她還要裝下去,我很對這女人很慪火,沒有說話,我伸下手去開始脫她那碎花輕薄裙子,她也不掙紮瞭,一直閉著眼,胸部起伏如波浪般,裡面是白色的貼身襯衣,我一並給她脫掉,露出白花花的身子來,隻穿著乳罩和內褲,平緩的小腹微微有點肉。
她閉著眼說:「關瞭燈吧?我怕」
我說:「不關,我要看見你,我要看著幹你。」
她不說話瞭,我把棉被扯過來蓋上,壓瞭上去。她伸手下去摸到我那裡說真大,我那裡已經硬得不能再硬瞭。
她還在嘟嘟嚨嚨地說:「老不死的要回來瞭,你可真大膽。」
我是大膽,這時候就算天王老子來瞭我也停不瞭。
當我要取下她的乳罩的時候,她聲音突然變瞭個調,嬌滴滴地說:「可不可以不脫奶罩?我好害怕。」
我選擇忽略這句話,直接扯瞭下來,雪白的奶子脫離瞭奶罩的束縛,晃晃悠悠的彈瞭出來。我忍不住伸出手握住瞭那飽滿,好軟,好像要證明它的彈性似的,這可是我日思夜想的寶貝啊。
我又捏瞭一把,然後俯頭含住那飽滿尖端的紅梅,吮吸著、舔弄著,雙手也握住那雪白的飽滿揉捏。這飽滿像是獲得瞭生命一樣,慢慢地堅挺起來,那兩顆紅梅也變得格外地精神,乳暈的皺褶擴散開來,變得更加飽滿平滑。
她一開始還是閉著眼,小嘴緊緊地抿著,可沒一會兒她就受不瞭瞭,臉兒潮紅,一雙黑眸更是閃著點點星光,小嘴也微微張開,輕輕地喘息著。我伸手脫下她的褲子,玫紅色的三角小內褲赫然顯露在我的眼前。
我卻並不著急,也不想直搗黃龍,我也知道要把女人先撩撥得起火的時候才進入。我拉她的手放在我的陰莖上,她熟練地套弄起來。我低頭吻住她的小嘴,兩人的唇舌彼此交纏著,她忍不住用手攀上我的脖頸,飽滿的胸部不住地隨呼吸起伏著,頂端兩顆紅梅鮮艷欲滴。
我伸手拉下瞭那玫紅色的三角小內褲,她臉一紅,雙腿難耐的蜷起,想要並攏。我怎能讓她如願?雙手掰開,整個人就擠瞭進去,用灼熱在她的嬌嫩的私處來回磨蹭,手指細細在她光滑的陰阜上畫著圈。
她覺得害羞,紅著臉他我:「快點幹啊,老不死的回來就不好瞭,快進來。」
我也不理她,把被子揭瞭,我要看著她那裡,看著我的陰莖擠開縫隙,慢慢推入的過程。
把雙腿搬得更開,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的花房,白花花香馥馥的肉饅頭,是我多少次在腦海裡浮現的樣子,和她的外貌不太相符,不知道我是何時聽到這樣的說法——女人的嘴巴大小和穴口大小是對應的,她的嘴巴算不上小的,可是穴口卻很小。
緊閉的小口已經濕潤瞭,那口子微微地張開來,隱隱露出裡面鮮鮮的肉餡,我忍不住用手撥弄瞭一下,花房周圍的肌肉像含羞草被觸碰一樣,很快地皺縮起來,再慢慢的疏散開來,像一朵正在舒展的玫瑰花。我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花瓣分撐開,裡面露出瞭粉紅的穴肉和迷人的皺褶,手指摩挲著那個銷魂的洞口,然後插瞭進去。
她用雙手把她的雙腿叉開使勁的拉往後面。這姿勢我才熟悉瞭,一開始就擺出「鳳翔」的姿勢,真是騷浪的行傢裡手。
我看紅瞭眼,撤出手指,左手扶著暴怒灼熱的欲望之根,湊近那洞口,把龜頭埋入兩片花瓣之間,蹭瞭蹭。她一直皺著眉頭,也許她是怕突然的疼痛,但是我不會那樣,因爲她的陰道濕潤還不夠,暴然而入會拉傷彼此的的組織。我扶著陰莖讓龜頭在花房淺處蜻蜓點水般蠕動,期待她的愛水泛濫起來。
她突然放開雙手,支起上身,伸手抱住我的臀部,猛地拉向她的胯間。我猝不及防,身子失去重心壓向她胯間,陰莖全根急速沒入,陰莖的包皮被她穴內的皺褶刮開,向後披翻帶來的微微的疼痛使我們同時叫瞭出來。木已成舟,我也沒法進行原有的計劃瞭。
我把她的散開的雙腿重新拾掇起來,推向她的胸部,用身體壓住,以使穴口向上,把她的雙手放到頭部,雙手支撐在她兩旁,用俯臥撐的姿勢拍擊開來,這樣抽插,才會次次到底。由淺入深,由慢到快,周而復始地抽插。
她開始浪叫,我知道這還不是她浪叫的時候,她的浪叫聲隻是爲瞭鼓勵我更深入的抽插她,更像是古代戰場上敲響的戰鼓。
她緊繃著臉,每抽插一下她的頭就使勁的向後伸長,露出雪白的勃頸。乳房隨著抽插,被撞擊得上上下下地跳動著,像一對調皮的兔子。股間的嫩肉給撞得「啪嗒」「啪嗒」直響,尖叫聲回蕩在房間裡,無所顧忌,沒天沒日。
我沉聲問她:「你喜歡嗎?你喜歡我的大肉棒嗎?」
她囁嚅著嬌聲說:「喜……歡……,比那老不死的硬多瞭,大多瞭呀,爽啊啊……啊啊……,別停。」
我像頭發瞭瘋的牛,亂沖亂撞。過瞭一會兒,我的脊背上滿是汗水,她的額頭鼻尖也滲出瞭細密的汗珠。肉穴這麼緊,這麼軟,這麼滑,水兒多得跟冒漿似的,越攪越多。兩人的雙胯間被汗液和淫液混合著濕透瞭,冒著騰騰的熱氣。
我密切地註意著我的感覺,以防那一刻提前到來。就在麻癢的感覺一波又一波侵襲著我的龜頭的時候,我提出要換姿勢,希望她擺出新鮮點的姿勢來。
她翻身馬趴著,翹起臀部,我一看就知道是「虎步」瞭,難道別人都看過那本書,都是那樣做愛的?
剛才被狠操的肉穴還在一張一合的顫動著,泛著淫靡的光輝。我估量瞭一下高度,叫她沉下來一點,她挪瞭挪雙腿,把雪白的屁股往下降瞭一點,我把那根灼熱狠狠地撞瞭進去,伴隨著她的尖叫聲一幹到底。
我也喜歡這個姿勢,看得見嫩嫩的、花瓣似的大小陰唇被肉棒帶著翻進翻出,別有情趣。她的頭垂放在枕頭上,斜睨著醉眼,看著交合的部位,嘴裡發出夢囈般的呻吟。
我伸手握住她搖晃的雙乳,趴在她的背上,用兩隻手指捻弄她的雙乳的乳尖,她興奮得搖動著豐臀,陰莖在花房裡緩慢的攪動,溫熱的肉穴和泛濫愛水把龜頭弄得癢麻難耐,我盡量地調整呼吸,來緩解射精的時間,可是我明白,我堅持不瞭多久瞭,我的感覺我清楚。
她問我:「我那裡什麼樣子?」
我喘息著告訴她:「像一支小小的飽滿多汁的玫瑰。」
她弱弱的笑瞭:「真的嗎?這是我在男人口中聽到的最美的比喻。」我突然覺得好嫉妒房東。
我告訴她我要射瞭,我的意思是我撥出來體外射精,她說:「你就射裡面吧,我上瞭環的。」
我直起身來,挺動著深深地撞擊她的嫩肉,加快瞭速度。她也挺動臀部,迎合著這抽動,嘴裡喃喃地說:「要死瞭,要死瞭。」
陰莖突然暴漲,一股濃熱的精液噗噗射進她的子宮深處,她如釋負重地軟癱下來,我附在她的後背一動也不動,陰莖還在她的陰道裡慣性地跳動,然後慢慢地萎縮,最後滑落出來,懶懶地耷拉著腦袋。
她的陰道一張一合地翕動,白色的液體從裡面慢慢地滴落下來。我覺得有點愧疚,射得太早瞭點,有點對不住她。
她轉過身來,用手指捻著我疲軟的陰莖,另外一隻手輕輕地拂瞭兩下,含嬌似嗔地罵道:「剛才不是這麼兇嗎?現在怎麼不行瞭?」
我笑瞭:「有這麼玩的嗎?」
她問我:「你和小敏做過幾次瞭?」
我說:「就一次,就是那天早上被你聽到的那次。」
她不相信地說:「騙人呢,那天早上我都聽見你前前後後幹瞭一個多小時,第一次會幹那麼久?現在一小時還不到,你怎麼這麼偏心眼哩?!」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瞭,到瞭她這裡,我就控制不住似的。
她說起瞭前夫,她老公雖然個子一米八幾,可是這方面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後來上煤場被埋瞭,換瞭這老不死的,就更不頂事瞭,說我做得很好。我倒是覺得很遺憾,我知道她還沒有高潮,我跟她如果梅開二度,我會做得更好。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瞭她,她突地跳起來說:「不瞭,今晚有點不舒服,估計月事要來瞭。」
我下床找來一條幹凈的毛巾,先把她那裡揩擦幹凈,把她擦幹後,也把自己擦幹凈瞭。她叉開腿咯咯地笑著問我:「你能幫我口交嗎?」
我還沒有那思想準備,覺得有點無法接受,老不死的陰莖經常在那裡進出,如果我給她舔那裡,豈不是有種給老不死的口交的錯覺?
我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我用同樣的話反問她:「你能給我口交嗎?」
她笑瞭,說:「可以啊,不過要先洗澡,洗幹凈瞭才可以的。」
我說:「我剛泡瞭溫泉回來,很幹凈的。」
她說:「不來瞭,下次還有機會的嘛。」
她爬起來到處找七零八落的衣服,這裡一件,那裡一條,好不容易找齊瞭,我看著她要穿衣服,就問:「你不在這裡睡瞭?」
她說:「不瞭,老不死的說不定幾時回來呢?」
我問她:「你不怕一個人瞭?」她訕訕地紅瞭臉。
她戴乳罩的時候,叫我給她扣好後面的鈎扣,我爲我能爲她做事而高興不已,雖然這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事情。她穿好瞭衣服,在下樓的時候雪我跟她說:「想我的時候就叫我給你修燈吧?」
她哈哈地笑瞭說:「這麼近,以後燈經常壞呢,你要經常幫我修喲。」
她摸索著噔噔噔下樓去瞭,我聽到她關門的聲音,想著剛才的激戰,在這方面,從敏到冉老師,我一直順風順水的,幹得酣暢淋漓,心裡也漸漸地膨脹驕傲,這是我第一次遭遇瞭滑鐵盧,感覺羞愧難當。我多想自己能做得好點,可是小寡婦那裡面的灼熱讓我受不瞭,她轉動臀部的頻率和敏和冉老師都不一樣,那麼的密集緊湊。
我不由得又想起《素女經》上面那段話來:「夫女之勝於男,猶水之勝火。」我那晚看的時候不以爲然,覺得自己不存在那種問題,連續多天以來的成功讓我自信心過分地膨脹瞭,原來「女人如水,男人如火」真的是至理名言,原來這是因人而異的,剛才是我太著急瞭,沒有好好地把小寡婦的欲火充分撩撥起來就開始幹瞭,小寡婦飽經沙場,非情竇初開的敏和年輕久曠的冉老師可比。
好瞭,下次還有機會吧,不過這次得瞭個教訓,讓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道理,我得好好的重新看待女人的身體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