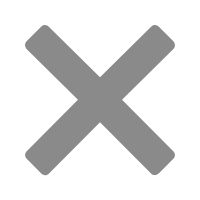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十六章 借箭
我不知道還能找誰,我曾經拒絕過她的幫助,可是此時此刻,我也隻能找他瞭,太陽快下山瞭,我加快腳步往教師宿舍就去。
這回我不用從後門,我從大門進去。上瞭二樓,正好遇見王老師獨自一個人在二樓上憑欄眺望遠處的池塘的水面,扭頭看見我來瞭,也不說話,還扭過頭去看那池面。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默默無言地走到她身邊。
很久很久,她才幽幽地說:「你去新學校瞭,有瞭新的婆傢,都不來看我瞭?」
我紅瞭臉低瞭頭說:「我這不是來看你瞭來瞭麼?」
她轉過頭用幽怨的目光盯著我說:「我的向非可真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瞭,恐怕你不是來找的吧?你要找的人兒在屋裡睡著的哩!」她朝房間裡面努努嘴,我的臉上一陣陣發燙。
她突然咯咯地笑瞭:「我說你是不是要回來瞭?」
我吃瞭一驚,到目前爲止,我隻把我的想法和敏說瞭,就再來這裡之前,她看著我臉上驚訝的表情說:「你也不要驚訝,我知道他們去找你瞭。」
我知道她似乎知道得更多,她停瞭停有點興奮地說:「你可真有膽子,都被你氣死瞭,這些老頭子平日裡驕橫跋扈目中無人。你當時真那麼幹的?」
我也不知道她從其他人那裡聽來的什麼版本,我也不好評價自己,說實話我心裡也有點後悔,她接著壓低聲音柔聲悄悄地說出瞭一個秘密:「他們就在剛才開瞭個會,校長好像真的不知道這個事情,把班主任批評瞭一頓,那會兒可真解氣呀!不過校長在會上說瞭,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你弄回來,如果連一個向非都弄不回來,他校長的威望和顔面何存?他當時就是這麼說的。你也知道,在樓下誰都得聽他的,連鎮長都要讓他三分呢?」
我的判斷沒有錯,他們不會放過我的,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臺階,所以我來瞭……
我看瞭看天色,鬱悶得都要大叫出來,其實我要的並不是這樣,我隻想安安靜靜地學習。
王老師嘆口氣說:「這些人的事,你是不知道的,表面上一副爲人師表帶貌岸然的模樣,背地裡盡是些見不得人的事,我說向非呀,你還是個單純的孩子,這樣搞下去對你沒好處。」
我知道她不是和猴子一夥的,我信她的話,我點點頭說:「是啊,我也在想這個事情怎麼辦才好哩?」
王老師似乎也知道我的想法,看著池塘中的倒映著飄逸變幻的火燒雲不再說話瞭,我感慨地說:「這些事一時之間就像這水中的雲朵變幻不定,還是應瞭古人那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話。」
王老師好像有點想傢瞭,眼裡泛著淚光,這時冉老師醒瞭,揉著惺忪的雙眼走出來說:「我還以爲是哪個呢?原來是你啊,抱著新學校的校花不要,專程跑來勾搭我們的第一美女來瞭。」
王來師漲紅瞭臉嗔怒地跑過去抓住她的臉說:「你這個小騷狐貍,一天凈是有的沒的滿嘴胡話,你羞不羞啊?人傢找你來瞭。」
冉老師紅著臉跑進隔壁她的房間去瞭,我很難爲情地木在那裡,王老師推著推我說:「快去啊,人傢都憋不住瞭,你還磨磨蹭蹭地幹什麼?」
我被王老師推著進瞭冉老師的房間,她順手把門給帶上瞭。
冉老師臉上掛著瞭淚珠扭頭不看我,看得我是又愛又憐,我去把她抱起來,她往我懷裡直鉆,不停地捶打著我的胸膛:「你都說要來的,你去哪裡瞭?你去哪裡瞭?」我柔柔地親吻她的雪白的脖子和耳朵,她便不打瞭,呼吸變得不均勻起來,在我耳邊耳語柔柔地呢喃:「我好想你,我好想好想要你……」
她把我推到床上,甩掉拖鞋,跨坐在我的大腿上,扯瞭被子蓋在身上。她擡起身子,俯下身來,親吻著我的脖頸,舌尖癢癢地舐過去。到瞭肩膀的時候,她在我的肩頭停住瞭,突然咬瞭下去,狠命的咬,鉆心的痛,我額頭上都冒出瞭汗珠,牙齒在忍耐中格格作響。
她終於松口瞭,說:「這一口要你永遠都記得我。」這一句讓我忘記瞭對她的憎恨和疼痛,心裡生出無比的溫暖。
她親吻著我的額頭,臉頰,找到我的嘴唇,把舌頭伸瞭進來。熟悉的香味,熟悉的溫度,熟悉的濕滑。我含住它的舌頭,舌尖纏繞在一起。她翻身馬趴在我身上,向下摸索,她卻迷戀這根粗壯,被她摸瞭摸,肉棍就越發顯得長顯得硬瞭。
冉老師將手握住我的命根,有些氣喘籲籲的:「王老師進屋瞭?」
我說不知道。
外面的天色漸漸朦朧起來,越來越暗,王老師房間的燈亮瞭,從走廊上反射進來些許微光。冉老師一邊套弄一邊說:「你真是來找的?!」
我說:「恩。」
她說:「誰信你哩,上次來你都沒有來找我?」
我說:「哪裡?」
她說:「王老師都跟我說瞭,你在她那裡睡瞭一宿。」
我說:「我隻是太累,被單洗瞭,我們沒有幹。」
她說:「騙誰呢,你會不幹?」
我說:「真的沒有幹。」
她說:「那你就幹我?」
我說:「恩,我隻愛你。」我本來想說「我隻幹你」,張口卻成瞭「我隻愛你」。
她說:「你們就那樣躺著,不幹?」
我說:「恩,就那樣躺著。」
她說:「唉,你這個傻蛋,要是我,我就幹瞭。」
我說:「你幹過。」
她說:「恩,用手摳過她那裡。」
我說:「哪裡?」
她說:「王老師平日裡一本正經的,心裡可騷著呢。她要我摳瞭又摳,不停地摳。」
我說:「她也摳你的吧?」
她說:「恩,你不來幹我,還不準她幹我呀。」
我心裡有些失落,王老師在我心裡面就像神那樣重要,她怎麼可能給冉老師幹呢?怎麼可能還幹冉老師呢?要是知道她是那樣的,那天早上醒來就該狠狠地日她,感覺好後悔。
在她溫柔的套動下,我的雙手也不安分起來,在她的背部肩頭撫摸著,抓捏著。隔著睡衣感受著她玲瓏光滑的身子。
我的雙手滑向她的臀部,試圖把她的裙子往上提,由於她的手在弄我的下面,裙子被手擋住瞭,提不上去,隻能露出屁股。我抽出右手,用指尖輕輕的從後面的雙股的縫隙間探進去,那裡已經是沼澤一片,陰毛上已經沾滿瞭液體。
她的身體已經在被子裡變得暖和,指尖被溫熱的的肉瓣包裹著,不安分地進出撇捺。指尖甚至能感受到肉縫裡最細微的變化,像一張口,時而微微翕開向外翻,時而緊緊收縮向內吸,吞吐著我的指尖,帶出的滑液在指縫間手掌裡流淌。
她直起身來,被子順著她的後背滑落,被子隻能蓋著我的腿和她的臀部。她把睡衣往上推起,從頭上面脫下來,雙手把長發攏在腦後。
夜色的微光裡,純白流線型的身體泛著白光,胸前烏黑的兩點是她的乳頭,周圍顔色比較淡一些的是乳暈……我看著這上帝的傑作,頓生此生何幸之感。
她用膝蓋支撐著身體,擡起屁股,留出多餘的空間。左手支撐在我的胸上,右手向後往下探到我的肉棒,用手指掬住那灼熱堅硬,挪動著臀部來靠近。我感覺到滑滑的肉縫漸漸地吞沒我燥熱肉棒的時候,仿佛整個身心已經被那溫熱給融化瞭。她直起身子,前後緩慢的搖動臀部。
我們都不敢發出聲音來,她用一隻手捂住自己的嘴巴,鼻孔裡冒著粗氣,我則是張開嘴緩慢悠長的喘息,隻有這樣延長呼氣的時間,喘息聲才會變到最小。隔壁還有她老公在睡覺,任何響動隨時都可能把他吵醒。
她開始變化成臀部轉圈的方式,像推磨一樣旋轉著,肉棒尖端傳來攪動的快感,愛水沿柱而下,流經我的雙股,流到身下的床單上。
我的指尖往黑乎乎的三角形的地方探索著,食指按著她的陰蒂輕輕地轉動,下體交合發出濕潤的「查查」聲就是從那裡傳出來的。肉棒在肉穴裡前所未有的興奮,仿佛一條不眠不休的蛇。
我伸出雙手去拉動她的大腿,才發現她已經身上經過這這些回合的運動,早已香汗淋漓,胴體呈現著霜晨一片珍珠色,氤氳一片漠蒙蒙的銀色水汽。乳房盈盈一握,在我的掌握中扭曲成形,婉轉成吟。囁嚅和喃喃的低微顫動的聲韻,夾雜著歡快的音調。
看到她扭動的身子如風中的柳條,我輕聲的問她:「你歇歇吧?」。
她不語,更加瘋狂地扭動著身體,直到她的肉縫一陣陣收縮。
我才知道她快要到達快樂之巔瞭,我央求她:「你停住,我們一起吧?」。
她才停住扭動,趴在我身上大口的喘氣。肉棒還插在她溫暖濕滑的肉穴裡面,我把它抽瞭出來。
她輕身低語:「別,我還要。」
我知道,我把她從身上撥翻下來,讓她躺在我身邊。她全身是汗,我怕她受涼瞭,伸手去拉被子來蓋上。
我俯下身來在她耳邊說:「你轉過身去,背對著我。」
她很聽話,她知道我喜歡從後面搞她。我從後背貼著她的身子,把她的長發理瞭一下,以防壓住扯動頭發弄痛瞭她。她豐滿的屁股直往到我的下腹蹭,我彎曲著身子,把她光滑圓潤的臀部挪到懷裡,用小腹包圍住。長長的肉棒不安分的戳動,似乎它要自己找到那熟悉的入口。
我一隻手穿過她的頸部,枕著她的頭,一隻手從後面擡起她的一隻腿,肉棒順著大腿根部緩緩的滑進。
她低低的呻吟瞭一聲,轉過頭扭著脖子看我,低低的罵:「狠心鬼。」
我的嘴唇貼瞭上去,下面開始抽動,她被封住的嘴裡發出支支吾吾的呻吟聲。
我知道我該怎麼做。等下面的兩個小情人都適應瞭對方的姿態的時候,我松開瞭她的嘴,把頭埋進被子裡。她一直不知道,我喜歡從後面搞她的原因,是因爲從後面搞容易發出淫靡的聲音,那聲音長短疾徐,風吟雨唱,慵懶中帶著快樂的舒卷……
我把頭鉆進被子,就是爲瞭聽這人間仙樂,肉體交合發出微微醉人的腥味和奶酪般的香味,混雜著汗液的味道,肉棒進出發出貓舔漿糊的噼啪聲,使我的肉棒更加長大。
我伸出頭來,看瞭看夜色中的她一眼,她雙手緊緊的抓住被子,嘴唇也死死地咬住被子,喉嚨裡發出嬌婉的低吼,我知道她快瞭,就再把頭鉆進去,在這淫靡的肉體撞擊聲中越插越快,越插越快,我的肉棒像根粗糙的樹幹,又像一把勤快的鐮刀,不知疲倦的收割這成熟的稻麥。我甚至能聽到肉瓣快樂的翻卷聲。
在這裡時間已經不重要瞭,我們做愛的時候如果還能認真地去計算抽插的次數,也就出賣瞭我們其實並沒有投入,並沒有快感。
我就這樣狠勁地浪插著,我也不知過瞭多久,我再次感覺到她的肉穴收縮抽搐,我的肉棒有一股電流從頂端傳遍全身。我狠命的往深處抵進去,緊緊地貼著她的臀部不動,一股熱流瞬間彌漫瞭我的龜頭,我在這股熱流的蠱惑下,一股勁道從大腿根部沿肉棒激射而出,我甚至能聽到那「咕咕」的液體奔流的聲音,我們繃緊的身子一下癱瞭下來。
如果說人間有什麼叫做解脫的話,我覺得此時此刻就是對解脫最好的詮釋瞭。
它已經和愛戀無關,和欲望無關,甚至可以說和天地間的一切都沒瞭關系,腦袋裡一片空白。
躺在床上,冉老師問我:「你這次來不會隻是爲瞭來幹我吧?」
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說實話瞭,她說沒問題。我們起床穿好衣服,一起去見瞭三一班的班主任唐老師,唐老師是個爽快的男人,滿口答應瞭。
我就知道他會答應,他在老學校帶著一個鴨子班,有說出的苦惱:每一次月考過後,三一班的第一名都要被三二班的要去瞭,再把三二班最差的學生換下來,如此輪番淘汰,弄得他苦不堪言,眼睜睜看著自己辛勤栽培出來的好苗子被別人挖走,而自己卻敢怒不敢言。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我就隻等一個人出現瞭,這個人就是校長,隻是我不知道這場等待是如此的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