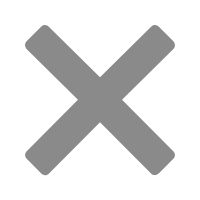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十七章 花開
我第二天照常去新學校上課,其實我有個更好的選擇,隻是可能性不大,這個選擇的關鍵在新學校的校長身上。我今天隻是來上課,名爲上課,實則是去見他的。
我沒有去上早操,我找到我在新學校的班主任郝老師,一起去見的校長。
到瞭校長辦公室,我們見到瞭他,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目光威嚴,穿著長筒鞋的男人,在我眼裡看來他的的確確像一個軍閥頭子,可是外貌往往是帶有欺騙性的,外表的強悍遮掩不住內心的懦弱。
我一五一十地把我爲什麼會來新學校讀書,老學校怎麼來要人的事跟他說瞭一遍,我的意思很清楚:如果他把握得住局面,我就不用走瞭。
不料他說出來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你要我怎麼相信你呢?你是老學校的第一名,也可以說是全鎮的第一名,他們是不可能會開除你的。你來我們學校,誰知道你什麼目的!不會是來打探消息,做間諜的吧?」
我當時就想把椅子劈頭蓋臉地甩過去,我幹他娘,有這麼做間諜的嗎?跑到你面前晃來晃去的找死啊?一個學校有多大的秘密可以保留,這還是個問題呢。我瞬間明白瞭他的懦弱,不過他也許是明智的,他怎麼可能會爲瞭區區一個學生,來得罪當地最有威望炙手可熱的人物呢?不過他的品德是低下的,卻找來如此卑劣的借口來掩飾他的懦弱,來糊弄一個來找他尋求庇護的無路可走的稚嫩的少年。
我沒有再說話,我知道說下去也沒有用瞭,他就是懼怕得罪老學校的校長,他就是這種慫人。
出來的時候郝老師很難過,他還在給我想辦法:「要不我們去縣教育局告狀吧,學生選擇在哪裡讀書是他的自由,你有這個權利。我聽說明天縣教育局有人下來瞭,到時候我跟你去,把情況反映一下,看他們怎麼說。」郝老師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他在爲我打抱不平。遺憾的是,跟我一樣太過幼稚,對形勢的估計太過於樂觀。
這一晚我想瞭很多事情,敏來找我,我什麼心情也沒有,飯也懶得吃,連說話我都覺得累,我覺得我快要對不住阿姨瞭,我叫她回去瞭。我下樓去街口花瞭三塊錢買瞭一包「古陶」牌香煙,沒有過濾嘴的那種,跑到閣樓上狠命地抽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抽煙,嗆人的煙味嗆得我直流淚,一個人在閣樓上關瞭燈,任由沉沉的黑暗將我包裹。煙抽完瞭,我還沒有一點困意。鬧鍾的指針很快指向瞭十二點,我依然清醒如白晝。我下樓來帶上門,帶上手電筒,往老學校的教師宿舍走去。
還好,王老師還沒睡,我不是來找冉老師的,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想找王老師,我知道她最疼我,我想在她身邊會好過一些些。
我敲開門,王老師一臉的驚訝,她穿著睡袍,已經準備開始睡覺瞭。她看見我哭喪著臉,什麼也沒說,轉身去倒瞭一盆熱水,自己鉆到被子裡去瞭。
我洗完腳,脫下沉重的衣服,拉滅瞭燈,在黑暗中貼著她躺下。
她還像那天一樣,從後面伸過手來默默無言地抱住我。不知道爲什麼,平生第一次,我哭瞭,眼淚肆意地在臉上縱橫交錯,王老師把我抱得更緊瞭。
我是她的孩子。她的溫暖蔓延開來,仿佛寒冷的冬天裡的一星火苗。她就在我身邊,我轉過身緊緊地擁著她,這天晚上我不止一次的想,要是我和她早生幾年,早點和她相遇,我們會不會成爲一對?我這些天來一直像隻狗一樣地四處奔走,我的確是太累瞭,太累瞭,我需要休息,我很快迷迷糊糊地睡著瞭。
半夜裡,我被一陣「砰砰」的敲門聲吵醒,心想誰這麼晚還登門拜訪?真是神經病。我搖瞭搖王老師,王老師醒過來瞭,卻是隔壁的人起來打開房間門。
門一打開,一個男人的聲音粗聲大氣地吼道:「這麼久才開門,是不是在偷人?」
我一聽這聲音,原來是隔壁的羅老師回來瞭,好想喝醉瞭酒。這傢夥半夜回來查崗來瞭。
女人委屈的說道:「這麼大半夜的,來都不打個電話來,你說我偷人,屋裡就有一個呢!」
男人氣喘喘的說:「哼,什麼玩意啊?」
女人好像生氣瞭,大聲地叫道:「不信你找啊!」
濁重的腳步聲在隔壁房間轉悠,伴著生氣時粗重的氣息,仿佛在找著什麼。
我聽見女人又說:「還有床下面沒看呢。」
然後聽見衣櫃子「吱呀」打開的聲音,女人又說:「櫃子裡面也看看。」
我猜想男人一定很尷尬,沒想聽到男人無賴的說:「親愛的,我開玩笑的呢,我老婆這麼賢淑,怎麼可能做那種事情呢?」
女人反駁說:「那也說不準哦,你七八天不見影兒,我就是找一個藏在房間裡,你也不知道啊。」
男人惡狠狠地說:「你敢?你敢我打爛你下半截來!」
女人嬌聲說:「你要是不來的話,你看我敢不敢?」
男人聲音變得柔和起來:「我這不是來瞭麼?」
接著聽到什麼物體被重重的摔到床上的聲音,伴隨著女人的尖叫:「害饞癆,狐貍尾巴漏出來瞭吧?」
男人嘿嘿的啞笑,應該是直接摸進女人的下面瞭:「騷貨,內褲都不穿,萬一來瞭盜賊,豈不是撿瞭個便宜?」
聽到這裡,我的下面那傢夥硬梆梆地直翹起來,我轉頭看瞭看瞭看王老師,什麼也看不見,屋裡黑洞洞的沒有一絲光,不過我清晰地感覺到王老師的呼吸變得急促,變得不均勻起來。原來偷聽的不止我一個。
隔壁的女人的呻吟聲越來越大聲,嬌喘得越來越急促,欲迎還拒的話語撩撥著我們的心房:「別……那樣……癢死瞭……不……舔……」,聲音斷斷續,含混不清,我試圖聽清楚每一個字,卻變得越來越困難。我隻好把頭擡離枕頭,,使聲音能順暢地傳到我耳朵裡來。
王老師的手不知什麼時候像條溫暖的蛇一樣蜿蜒過來,鉆進我的內褲裡,輕輕地握著我的勃起。
當我繼續聆聽這人間妙樂的時候,女人突然驚醒似的發話瞭:「你這頭豬,門還沒關!」
原來她現在才知道門還沒關,隨之而來的是關門的聲音。我見過羅老師的女人,平時板著臉一副一本正經的模樣,在床上卻這麼淫浪,讓我覺得分外的刺激。
腦海裡此刻卻是不停想象著王老師的赤裸的樣子:肌膚純白潔潤,素手如剝蔥那般,纖纖細細,粉面玉頸,乳峰高聳,修長的雙腿如新生的蓮藕,艷麗光彩,苗條動人。在我的想象裡,我總想把最美好的句子用在她身上。
裡面傳出「噗滋」「噗滋」的抽插聲,他們已經進入正題瞭。我是如此地迷戀,我的心提到瞭嗓子眼,女人的手在下面微微蠕動著,頂部已經有粘液流出。
我也不清楚我害怕什麼,有種恐懼在心裡,我怕這撫摸,我怕失去我最美好的聖潔的企盼。
男人一下又一下的撞擊,從聲音可以聽得出來動作有節奏而且連貫,「噼噼啪啪」的清脆撞擊聲和女人婉轉而銷魂的呻吟聲回蕩在房間內。女人的呻吟時斷時續,時高時低,撩撥著我敏感的神經,王老師的手不知不覺已握著那條灼熱的勃起輕輕套弄。
此刻隔壁的女人已經完全沉沒在瞭性愛的泥潭裡,失去瞭理智,毫無顧忌的呻吟起來。男人壓抑著自己的聲音,低吼著喘著粗氣嘟噥著:「你小點聲,小點聲!隔壁會聽到的。」
原來他們也知道隔墻有耳的呀!
拍擊聲暫停下來,估計是變換姿勢瞭,可惜看不見換的什麼姿勢,木床「嘎吱,嘎吱」的響動。忽然女人悶哼瞭一聲,伴隨著「噗嘰」的肉體摩擦的淫靡聲音,應該又插入瞭,接著人每一次輕微的呻吟都伴隨著「噗嘰」的聲響。
我似乎能想象得到她那多汁的蜜穴的模樣,像吐著白色乳漿的泉眼。我爲自己想到這個比喻興奮莫名,喉嚨緊瞭一下,重重咽下瞭一口唾液,心裡還在「砰砰」的跳動,臉頰像著瞭火一樣滾燙。由於聽得過於投入,始終保持一個姿勢不變姿勢,擡起的脖子有點酸。
這時女人說話瞭:「親愛的,你快點射吧,我受不瞭瞭!」
男人說道:「你在下面吧,我要射你肚皮上!」
清脆的「噗滋」聲再次活躍起來,聲音更大,陰莖抽送在女人的陰道裡,隨著愛液「咕滋,咕滋」的響瞭起來。
女人此刻似乎完全迷失瞭自我,大聲忘情的呻吟開來,「啊……啊……哦……哦……哎呀!」
木床被擠壓得「咣當、咣當!」直響,震蕩著整個房間,波及瞭隔壁的我們,聽得出來男人的動作越來越粗魯,越來越生猛。我心都要跳出來瞭,我相信這對男女此刻隻要點上一把火,熊熊的火焰就可以燃燒掉整個宇宙。
也許是女人的叫聲過大瞭,可能男人有所顧忌,用手捂住瞭女人的嘴,女人隻發出說不清痛苦的還是極樂的「唔唔唔」的聲音,混雜著男人的喘息聲,混雜著清脆的肉體撞擊聲——
「咕滋……咕滋……咕滋……啪啪……咕滋……咕滋……咕滋……啪啪」,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男人「嗯」瞭一聲說:「來瞭,撒開手,別抱住我。」
緊接著男女都開始急促的喘氣,男人很粗聲地喘著:「啊……啊……啊……」,估計是正把精液射在肚皮上瞭。
女人卻嬌滴滴的埋怨:「都射在人傢嘴唇上瞭。」
我的天,射這麼遠,不知道女人伸出舌條舔瞭沒有。
女人說:「親愛的,你真棒!打電話叫你來你都不來,你有那麼忙嗎?」。
男人說:「想來來不瞭嘛,你以爲我不想你?」
女人說:「騙子,騙子,拿紙來!」……緊接著是拉滅電燈的聲音。
我轉過身來,把手伸向王老師胸部,「王老師,可以嗎?」
王老師沒有回答我,松開瞭手,起身拉亮瞭燈,在床上坐瞭起來,怔怔地看著我,像不認識我似的。她的目光讓我的臉發燙。我爲瞭避開她的目光,扯上被子來蓋著我的頭,我害怕她說出那個字,那樣的話,我就徹徹底底失去瞭她。
王老師終於說話瞭:「窗簾還沒拉上。」
我狂喜著,趕緊鉆出被子去把窗簾拉上。
回到床上,王老師悠悠說:「不要叫我王老師,叫我玉姐。從今天起,我已經不是你的老師瞭。
我把顫抖的手伸向王老師腰際的睡衣下擺,她輕輕擡起瞭雙臂,我把她的睡衣撈起脫瞭下來,裡面是同樣雪白的吊帶內衣,緊繃繃地貼在她的乳房上,呈現自然完美的半圓形。
看著這個身上隻剩吊帶和內褲的女人,我的心就像小鹿亂撞似的就快跳到外面來瞭。她嚶嚀一聲撲倒在我懷裡,羞紅瞭臉龐,此時此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個壞人,心裡充滿無限的感激。
「向非……你怎麼瞭?我不好嗎?」她擡起頭不由有些奇怪地問,因爲我隻是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
我回過神兒來,她正眨巴著眼睛迷惑不解地望著我。
我說:「你真好!」
我輕柔小心地把她放下,平躺在床上,俯下身子看著這渾然天成的美人兒。
她纖纖的手指好奇地掃過的胸肌,「好硬啊……怪不得冉老師一直說很喜歡。」
她感嘆地說著,輕輕地掬住我的乳頭。
我說:「冉老師說的?」
她說:「恩。」
我說:「什麼都說瞭?」
她說:「恩。」
她雪白的肌膚如絲綢一樣光滑,我們之間終於赤裸相對瞭,再無任何阻隔。
她說:「那天早上我以爲你要幹我?」
我說:「我沒那樣想。」
她說:「那你現在就想?」
我說:「那天我幹你,你會讓我幹嗎?」
她說:「會啊,我一直等著你,可是你卻不行動,我那裡都濕瞭的。」
我說:「現在呢?」
她說:「濕瞭。」
她抓著我的手,引導著我的手,覆上她挺翹的乳房,雖然有一層吊帶相隔,我還是清晰地感覺到瞭急促的心跳。我解除瞭她上身的最後束縛——一對熱烘烘的奶子如白兔般脫跳而出,乳房很大,看上去好像幾乎不受重力的影響,完美的半球形,看得出來已經成熟。嫣紅的乳頭不太大,如熟透瞭的櫻桃一般嬌嫩誘人,優美地朝向上方,就像追逐著陽光的藤蔓植物的嫩芽。
她閉著雙眼急速地嬌喘著,芳香少女的氣息噴在我的臉上。
我躺在她的胸上,貼緊著她乳房呼吸著這體香,像一個乖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裡。我的身上都出汗瞭,熱烘烘的難受,我什麼都清楚,清楚地感到她乳房的溫暖,清楚地感到她腹部的呼吸。我睡在她身上,就像一個嬰兒在做夢中蠕動,這種肌膚相親的感覺讓我産生合二爲一的錯覺——她中有我,我中也有她,永不分離。
我在她的胸前撫摸著抓捏著,細滑柔膩,兩團軟肉在我輕微的揉捏下,歪擠開去,變換著形狀。她的乳房在鼓漲,就像海潮湧起的欲望,越來越高漲,似乎要將我吞沒,讓我有種悸動的不安。
「嗚……啊……」她壓抑的嬌吟終於從齒縫間迸發出來。
這呻吟聲提醒我註意到瞭她寂寞的嘴唇,我用一個長長的吻,打開她的嘴唇。我早就該這樣做瞭,我緊貼著她的嘴唇,不留一絲一毫的縫隙,把舌頭往她咽喉裡伸,在她的嘴裡攪動另一片香軟糯滑的舌頭,一會兒進去一會兒又退出來。
「玉姐,你今夜好美……我愛你……」我的唇在她身上忘情吸吮每一塊芳香聖潔的地方,唾沫沾瞭她一身。
「非,今夜你就是我的王,我就是你的女人。」她再次凝望著我,迷亂的眸子又有瞭一層水霧。
蕾絲內褲也是純白色的,邊緣有一纖細的小花,如人一樣冰清玉潔。在熾熱的電燈的光線中,我拿走她最後的遮羞佈,我用兩個指頭分開她的縫隙,像剝開一個珍美的小桔子似的,好奇地看著那裡:那縫隙粉粉嫩嫩地陷進去,兩股間那一坨那麼飽滿。縫隙合攏的時候就是一條白白的縫,幾乎會忽略它的存在;縫隙分開時,就看得見那細小的酒紅色的唇瓣,和裡面細細的肉的皺褶,還有那交接處一星嫩蕊。它像受到羞辱一般,微微膨脹起來紅瞭臉,細細的嫩嫩的花蕊微微鼓起,那麼甜美,那麼濕潤。輕輕觸及它的時候,就激起瞭她夢中的叫喊。
我用一根手指探尋進去,感到瞭那裡面的緊張,像嬰兒的小嘴吸吮著我的手指。這裡和小寡婦的不一樣,沒有小寡婦的那麼光潔,這上面還是有毛的;這裡和冉老師的不一樣,沒有那麼多毛,也沒那麼雜亂,整整齊齊地從陰阜上倒立著往上長,兩指寬黑亮亮的一溜都快延伸到小腹上瞭;這裡和敏的不一樣,就算敏長到她這個年齡,敏的應該是三角形狀覆蓋在上面,山丘下卻和敏的一般圓潤光白。
我用手指熱烈又細致地刺激著她,她脆弱而又有力的呻喚聲在房間裡飄蕩。
我把她拉上來,拉到我的大腿上來坐著,她的臉偏向一邊問我:「你是這樣幹她們的。」
我說:「她們?」
她說:「恩。」
我說:「不是的,這是我在書上看到的?」
她說:「書上有?」
我說:「有」
她說:「你沒用過?」
我說:「還沒來得及用。」
她說:「這叫什麼名字?」
我說:「叫‘鶴交頸’」
她說:「不對,這叫‘古樹盤根’……」
我說:「你怎麼知道?」
她說:「我會。」
我無法避免這狂熱的挑逗燃起的欲望,忍不住挺起矗立的尖端撫愛著她那裡,她直起身來,扶著我寬寬的肩膀,扶著那享樂的神經,緩緩地沉下身去,發出輕微的叫喊,那甘美濕潤直達我的心底。
她喘著說:「你是我的瞭。」
我說:「不是她們的?」
她說:「不是。」
我說:「那怎麼辦?」
她說:「隻和我幹。」
我說:「你願意?」
她說:「願意。」
我說:「爲什麼?」
她說:「真大,真硬,裡面慢慢地舒服。」
她便款款地搖動起來,微微喑啞的呻吟的聲音在漂浮,微微哽噎的聲音像一個又一個波浪。這無邊無際的波浪,甜蜜得讓人渾身通泰。
我不願這一切結束,我壓住翻騰著的欲望之泉,溫柔地迎來送往。伊人相依偎,耳鬢廝磨,堅挺的乳房來回摩擦著我的胸肌,一剛一柔,一進一退,一股微癢的酥麻感漸漸在悄然聚集。
她親著我,在我的耳邊顫抖著說瞭一句:「我愛死你瞭。」
我說:「真的嗎?」
她說:「真的。」
直到一陣電流刺穿我的全身,我的腹下突然卷起一股風暴,席卷瞭一切,我顫抖著噴射而出,把快樂深深埋種她體內。幾乎同時,她也忽然擡緊摟住我,呼吸停止,那裡急速收縮,也湧出一股濃熱。我們久久地相擁著,抱著她,就像抱住瞭整個宇宙,不再害怕……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她說我睡得像石頭,一動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