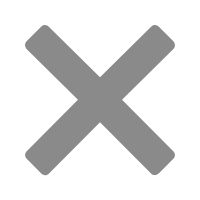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十八章 是夢終空
第二天晚上,我和郝老師一起去見縣教育局的領導。打瞭幾通電話,最後是在一傢便民飯店找到的,這是一傢從外面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便民飯店。可是到瞭裡面,卻極盡奢華,也許這是專門爲他們這些特殊的「便民」準備的雅間吧。
幾個縣教育局下來的領導正在和鎮裡的領導開懷暢飲,個個頭肥腦滿,油乎乎的頭面,喘著粗氣,扯直脖子哇哇亂叫。一人抱著一個濃妝艷抹的妓女在勸酒,好把妓女灌醉瞭弄到床上去,不開錢就幹瞭走人。
我有種預感,覺得這事肯定辦不成,郝老師說:「既然來瞭,就試試看吧?」
在門口小心翼翼地叫瞭叫。這時晃晃悠悠走出來一個人,粗聲大氣地問:「什麼事?」
班主任滿臉恭敬的想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話還沒說完,這個狗日的就大聲地說:「沒看見我們在忙嗎?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我拉著班主任就走,班主任漲紅瞭臉,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如果連校長都保不住我,找這些飯桶殺豬匠又有什麼用呢?不就是回去嗎?這個臉我丟得起。我也不願讓郝老師受這窩囊氣,雖然他隻做瞭我三天的班主任,可是卻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班主任。
不到最後一刻我是不會放棄的,我照常去新學校上課,雖然我知道我已經不是新學校的學生瞭,但是如果我不裝作若無其事地上課,我就失去瞭和老學校談判的籌碼,這點我比誰都清楚。我隻是等待那一刻的到來。
不過今天真是倒黴,終於被「雙龍幫」的人找上來瞭,放學的時候剛走出校門,呼啦啦二十多人,一下子像猙獰的野獸一樣,從卡車後面,從垃圾桶旁邊,從角落裡如潮水一般匯聚起來,揮舞著鋼管水果刀木棒,朝我撲過來。
我撒腿就跑,跑過大街小巷,跑過田野,拼命地急速邁動雙腿,這腿仿佛就快不是自己的瞭,跑得大汗淋漓,終於甩脫瞭這幫可惡的蒼蠅。
爲瞭我的計劃,我還是每天堅持去上課,每天都被人追趕,我真的就像一頭喪傢之犬瞭。我書包裡有刀,我卻從來不拿出來,這麼多人,拿出來也沒用,就算砍翻一個,又會上來一個,還好我跑得夠快,我像豹子一樣突突地奔跑,就這樣拖瞭好幾天,還不見老學校的校長到閣樓來,我再也熬不下去瞭,我離開瞭新學校,再一次輟學瞭。
不知道爲什麼,這一次我居然沒有太難過,也沒有太悲傷。如果我的計劃不能實現,我可能就真的離開這裡瞭,我的舅舅在另外一個不遠的鎮上,他那裡也有中學。但是我有種很強烈的預感,就快瞭,就快瞭,我隻需要要耐心。
敏每天都來陪著我,看著我不開心,她也很不開心,隻是默默地陪著我,她相信我的感覺是對的。
阿姨幾次叫我去傢裡吃飯,我都沒有去,我不知道怎麼面對她。不過我的日子過得更簡單瞭,更自由瞭,我不用踩著上課鈴聲進教室上課,我愛什麼時候學習就什麼時候學習,不必再擔心遲到,也絕不會「曠工」。
除瞭吃飯、睡覺、拉屎、洗澡、鍛煉身體。我的愛好就剩下做愛瞭,很多時候都和敏做,我給她換姿勢。有時候去找王老師,有時候去找冉老師,有時候偷偷地和小寡婦幹上一回。
這些所有的事都厭倦瞭,我就背著裝著砍柴刀的書包上街去,像電視裡演的獨行的刀客,滿大街找「雙龍幫」的人,看見一個弄一個,看見兩個弄一雙,看見三個或者三個以上我就跑,追得酣暢淋漓,跑得酣暢淋漓,像隻瘋狗那樣,逃跑和追逐對我來說沒有多大分別,反正都是跑路,就像做愛那樣,被幹和幹人都一樣會高潮。
等待是讓人絕望的,當你無所謂的時候,當你絕對無所事事的時候,某種黑暗的邪惡的力量就會爆發出來,它會讓你勇往直前,無所畏懼。
就這樣過瞭十多天,紙最終是包不住火的,十多天之內我回過一次傢,被爸爸罵瞭個狗血淋頭,還想動手打我,在母親的庇護下我奪門而出,急匆匆地就回來瞭。
終於在一個傍晚,我正在院子裡端個大碗狼吞虎咽,敏在閣樓上寫作業。校長終於來瞭,帶著正主任副主任來瞭。
我不知道當時我是什麼感覺,大概是既期待又厭惡。我雖然需要他們幫助,但是也是他們,才讓我如此狼狽,極度糟糕。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敏趕緊下樓來,去屋子裡端瞭板凳出來招呼他們坐下。
校長開口就說:「你的事情我並不知情,都是下面的人在搞鬼。」這還像句人話,一句話先把自己的責任撇幹凈,不管這話是真是假,但是聽起來順耳。
他說:「你回來吧,不要在這樣下去瞭,這樣會毀瞭你。」
我沉吟不語。
他問:「你還在顧慮什麼?」
我說:「你知道的,我不會再去三二班瞭,我要去三一班。」
他說:「沒問題,在哪裡都是一樣,你還是第一名。不過這得問問三一班的班主任唐老師。」
這個關節早在我預料中,我早已經打通瞭。
我又提瞭一個條件:「這是我女朋友,新學校的。她離不開我,我去三一班的話她也要去,不能收她的任何費用。」
校長大氣地笑瞭:「這算什麼什麼條件呢?明天來上課吧。」
他說:「一切都過去瞭,回到以前,重新開始,安安心心地學習。」話都說到這份上瞭,我還能說什麼呢。
我仿佛被三二班驅逐瞭好多年,今天我又回來瞭,不同的是:我來的是鴨子班三一班,還帶來瞭新學校如花似玉的校花。
我一時間成瞭老學校甚至整個小鎮上的風雲人物,大街小巷都在說著我的故事,好的不好的都有。有人說我浪蕩,有人說我豪邁,無所謂瞭,在我看來都是一樣的。我一直覺得,這事情是可以載入校史的,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再有瞭。
三一班的人很友好,這讓我感覺很安慰。他們隻是信心不足,「鴨子班」這個頭銜就像一個魔咒,就是孫猴子的頭上的金箍,限制著他們的潛力。我被驅逐過來瞭,他們的面貌煥然一新,就揚眉吐氣瞭,這就是標榜的力量,全班上下一片生機勃勃。而且重要的是,我不會再被三二班挖走,這就出現瞭一個奇怪滑稽的狀況:鴨子班有第一名,尖子班有平均分。
我拉攏瞭班上幾個體格健壯的人,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在「雙龍幫」那裡吃瞭虧,這是少不得的。閑得要死的時候我們就上街上去找「雙龍幫」的人,這已經成瞭我發泄旺盛精力的不良習慣。「雙龍幫」人多勢衆,隻不過大多數時候相當分散,我們見到人數少的就打,見到人多就跑。
青春就像一把春天的野火,嗶嗶剝剝,盲目地滿山遍野地燃燒著,燃燒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