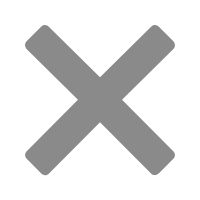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五十章:傷痕
「阿良,你似乎有些急躁。」
我仔細地打完瞭一套從飛龍寺僧人學來的「達摩拳」,感受著勁力從每一節關節和筋骨肌肉傳遞往四肢的細微流動,讓體內活躍的精氣四散,匯入軀體中,滋養著我的身子。
這是練精化氣的第一步,對我來說已是如吃飯喝水般尋常而自然的舉動。第二步則是以內功將這粗糙的,最本質的生命力進一步匯集,提純,升華,從而得到可控的,更高質量的真氣。當然,因為聞香散人一掌把我的丹田給打爆瞭,什麼丹田,什麼氣海,統統都沒瞭。沒有可以匯集精氣之處,沒有這至關重要的五臟六腑之本,我的精氣就像是無根之水,在我停止吐納和練拳之後便會自然而然地散入我的身軀,而不是真正地為我所用。
更何況我的經脈被走火的真氣一陣沖撞,雖然明面上沒有什麼跡象,但是實質上已經殘破不堪。哪怕隨著時間與細心的調養可以補救一些,但是幾乎沒可能進行完整的周天行氣。
其實這就是普通人習武鍛煉從而增強體質的方法,但是比起內功與真氣的效率,簡直是天壤之別,讓適應瞭那種修煉的我對於回到這種效率低下的方法極其不適。
我收拳後,揉瞭揉隱隱作痛的腹部,對身旁靜靜觀看的中年僧人說道:「也許吧。寺內的款待非常熱情,但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傢。我想回傢瞭。」
僧人說道:「你確實比我想象中有耐心。尋常的病人在能夠下地行走之後,沒有任何一個像你一樣能夠等到完全治愈才提出這個要求的。」
我笑瞭笑,說道:「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怕死吧。不過說真的,這段時間確實多虧瞭宗興你和圓海住持的關照。沒有你們的幫助,數月前我肯定已經死瞭。此等大恩大德,韓良此生必然銘記於心。」
宗興欣慰地拍瞭拍我的肩膀說道:「你不必如此想。飛龍寺隻是做瞭它該做的事。之後的,都是你自己的努力。」
我看著宗興的國字臉,有些感慨。飛龍寺並不大,一共才不到十五個僧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從小在寺裡長大的。身材魁梧,濃眉大眼的宗興是少數半路出傢的僧人,曾經混跡過江湖,因此與我甚是投緣。他是飛龍寺裡為數不多的武僧,也負責寺裡的外務。
兩周前,在我的身體終於恢復到能夠進行相當激烈的運動後,我跟他每天都會試手對招。他的武藝相當精湛,我推測他的戰力至少有三流中的好手之境,可能隻比受傷前的秦喜差上一籌。
「……阿良,你回去之後有什麼打算?」
「生活方面倒是不需要擔心,我從來都不是靠武力過活的。不過,嘿,既然青蓮教送瞭我這麼一份大禮,那麼禮尚來往,我也得繼續找他們的麻煩瞭。」
宗興擔憂地看瞭看我,說道:「阿彌陀佛,我就怕你這麼說。阿良,你我雖然隻相識瞭三個月,但是我覺得我必須告誡你,不要讓仇恨蒙蔽瞭你的心。這是一條危險的路。」
我打趣道:「我就知道你老是拉著我去跟圓寂大師打機鋒是有原因的。放心吧,我清醒得很呢。這幾個月我花瞭很多時間去思考這件事,甚至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想得最多的一件事。」
宗興嘆道:「正因如此,才更為危險啊。怨嗔癡,施主你的心已被嗔恨所填滿,但是卻仍然保持著冷靜。不是入魔勝似入魔,這是最為危險的。」
我哂笑道:「宗興,佛傢的道理有很多我認同和欽佩的地方,但是道理是道理,人是人。我恨青蓮教和它所對我做的一切,恨得天經地義,哪怕是佛祖降世也無法開解我。也許有些人可以從放下和覺悟中尋得安寧與解脫。但是我嘛,我是那種以牙還牙,以血償血的人。若不是那樣的話,那我就不是我瞭,而是又一個迷失於苦海的傀儡。」
宗興飽歷風霜的臉上有一種我難以解讀的表情,似是悲憫,又似是物傷其類的共鳴。
「阿彌陀佛,阿良,你的心意已決,我無法改變。但是作為朋友,我隻希望你不要迷失自己。」
我笑瞭笑,想要自信地告訴宗興自己不可能那麼軟弱,但是對上他誠懇的目光時,卻不由自主地想起瞭之前我情緒失控的那種自由感,那種放開束縛的肆意。我從未想過,讓自己沉浸在憎恨與怒火裡,竟會有如此安寧的舒心感,讓人想要沉溺於那放肆的情感中。迷失自己原來不是一件令人彷徨不安的事,放開辛苦地控制,壓抑住的一切情緒,竟是如此美妙。
宗興說得對,這種深藏在我心中的情感,濃烈而熾熱,強烈得讓我甚至有些恐懼。我自認不是一個情感非常激烈的人,而是相當理性,乃至超然的人。但是這次的位面任務讓我意識到,我對自己的認知有些膚淺瞭。也許在這一切發生之前,當自己心態平靜,用理性剖解一切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不會被仇恨沖昏頭腦。但那是因為生活在平和富足的現代社會的周銘根本沒有緣由去真正地憎恨,去全身心地想要毀滅什麼東西,想要殺死一個人,才能自以為是地超然。
而現在的我有瞭。
但是我不該,也不能就這麼沉入自艾自怨的心情裡,讓聞香散人留下的傷害定義我的一切,將韓良這個人的生命,身份,從此就鎖死在一個受害者身上。
我悄然握緊瞭拳頭,對宗興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謝謝。我不會停止復仇,但是我會盡全力不讓它成為我的一切。」
也許我永遠無法徹底除去這次慘痛教訓的陰影,但是我不會讓它戰勝我。
宗興點點頭,笑道:「別忘瞭,你隨時可以回來這裡,靜靜心。住持可喜歡你瞭。」
我沒好氣地說道:「住持和所有那些喜歡告訴我我有」佛緣「的人我都是敬而遠之的。我可當不瞭和尚。」
「真的不考慮一番麼?你已經吃瞭三個月的齋瞭,經學也學得比寺裡幾乎所有的弟子輩還好。」
「別說瞭,我要在自己徹底忘瞭肉味之前趕緊還俗。」
「好吧……越城那邊的藥草供應應該不會有問題。我知道你的傷勢雖然已經恢復得差不多瞭,但是傷痛可能很久的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完全消失。別老是硬撐,該用藥就要用藥。」
我下意識地摸瞭摸腹部,答道:「我有分寸的。」
數日後,薛府派瞭人來護送我回越城。與宗興和圓海住持告別之後,我與來人一起啟程離開。而薛府派來的正是我最想見到的那個男人——唐禹仁。這次他帶瞭一小隊武裝到牙齒的護衛,看來上次的慘痛教訓確實留下瞭印象。除此之外甚至還拖瞭一輛馬車,顯然是擔心我的身體無法承受那八百裡路途的負擔。老唐啊老唐,真是個面冷心熱的男人。
看到那個缺瞭左臂卻精神不錯的好友,我激動地與他擁抱在一起。唐禹仁雖然臉色有些蒼白,但是眼神依舊凌厲,沒有我所擔心的頹廢和死氣。
「你這傢夥……一走就是三個月,我可擔心瞭。沒事吧?」
久別重逢,唐禹仁的撲克臉也難得地露出瞭由衷的笑容:「你也是,看來恢復得不錯。咱們上馬車說話。」
馬車緩緩地在官道上開始動起來,我和唐禹仁入座後,他饒有興趣地對我說道:「你不會是客串瞭幾個月的和尚瞭吧?怎麼頭發這麼短?」
我摸瞭摸自己清爽的短發,說道:「我看寺裡的師父在給人剃發,就順便求他幫我剪瞭剪。說實話,我一直不喜歡留長發,太麻煩瞭。」
「江湖兒女倒是不必拘泥於這種小事。」
「過去這四個月我除瞭每個月薛府來人給我捎信之外,基本上與世隔絕的。怎麼樣,情況如何?」
唐禹仁長長地嘆瞭口氣,說道:「沒有進展。秦喜跟我說瞭你的推論,我也覺得寧王府最有嫌疑。我們針對它展開瞭一些調查,但是寧王府反應很快……甚至可以說是早有準備,一套連消帶打讓我們的行動極其不便。雖然這種迅速的反應隻會讓知情人覺得更可疑,但是懷疑是懷疑,就算我們有薛府和玄蛟衛背書,也沒法對皇上的親叔叔做什麼。」
「有持無恐啊……真是令人不爽。」
沉默瞭片刻後,我又開口問道:「秦喜有沒有跟你說起我那條定能讓他們敗露的妙計?」
唐禹仁有些煩惱地搖瞭搖頭道:「妙計……你那是絕戶計。不到最後關節不能用。」
我聳瞭聳肩道:「那我就沒轍瞭。對手是這種體量的存在,不搞狠一點是起不瞭波瀾的。我左想右想都沒有比這個更有用的做法瞭。你們那邊我猜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吧?」
「是的。通常到這種時候就輪到玄蛟衛用點陰險手段瞭,但是對方身份尊貴,我們束手束腳的,很難搞。」唐禹仁揉瞭揉眉角,似乎有些疲憊。
好傢夥,不愧是大燕朝廷陰暗面的精英,這麼隨意地就把這種嚇人的話說瞭出來。
「嘖,既然都沒有頭緒,那先不聊這事瞭,頭疼。話說……你的傷勢恢復得還好吧?」我話鋒一轉,小心翼翼地提起瞭這相當敏感的話題。
唐禹仁摸瞭摸那空蕩蕩的袖子,自嘲地笑瞭笑:「好是好瞭,可殘也是殘瞭。這身辛苦練就的武功算是廢瞭大半。還好不是右手,不然的話我的覆海針也隻有七成功力瞭。你和秦喜也是吧?他是我們這一輩玄蛟衛刀法最精湛的,若非根骨有憾處,早就晉身二流之境瞭。你則……」
我把唐禹仁不忍說出的那句話說瞭出來:「今生再無修煉真氣的希望,從此就是個凡夫俗子。嘿,我倒還好,反正正式習武也不過兩年不到而已,何況我一直是靠智謀的。我比較擔心你和老秦。你們兩個是過著刀口舔血的生活的,武功大減可以說是關乎到生死的大事……你們沒問題吧?」
唐禹仁有些失神地靠在窗口旁,掀起簾子看著窗外金黃色的莊稼,輕聲說道:「誰知道呢?一個沒有瞭武功前途的武力型玄蛟衛,和一個再也潛伏不瞭的細作型玄蛟衛,又有什麼價值呢?」
一時間,我倆有些無語,隻是靜靜地坐在馬車裡,聆聽著野外生機勃勃的聲響。
不知道過瞭多久之後,我斟酌著話語,開口道:「唐兄,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和內核是很復雜的東西。外界和自我的評價都是形成我們自我價值不可或缺的成分,也同樣作用於我們的身份和內心最純粹的自我。你覺得『唐禹仁』這個人,最核心的部分是什麼樣的,或者用一句佛教的話來說,他的『真我』是什麼樣的?是一個會因為武道路途被斬斷就失去前進方向的人嗎?是一個自我價值被他的武功,他玄蛟衛的身份,他的背景關系所決定的人嗎?如果失去瞭這些東西,他還是唐禹仁嗎?他就失去瞭自己最真實,最重要的內核瞭嗎??」
唐禹仁一開始聽著我說這些抽象又不著調的話,有些不解。但是聽到我最後那一連串的問題,他皺起眉頭,開始認真思考。
我靜靜地讓他想瞭一陣後,繼續說道:「在我看來,那些都是關於我所知道的那個唐禹仁,最為末不足道的細節。你的心性,你的堅韌,你的冷靜,你的隱忍,你那張死人臉下滾燙的熱血和心腸,你一諾千金的豪情,你對於自己近乎狂妄的自信,你從未因為我卑微的身份而對我不屑的平等心態。這些才是組成我所結交,敬仰的那個男人的本質。聞香散人可以打斷你的手臂,可以廢掉你的武功,但是他無法毀滅這些更為本質,更為純粹的東西,隻有你自己放棄瞭的時候,它們才會散去。」
我誠懇地看著身前的好友,說道:「前段時間我很頹廢,很憤怒,很焦躁,滿腔怨恨卻不知往哪發泄。但是宗興大師一直在開解我,想讓我知道,就算要走一條充滿瞭憎恨的復仇之路,也不要迷失自己。我覺得他的話有道理。哪怕我過去這三個月每個夜晚都會顫抖著被痛醒,我也要抓住那條不認輸的信念,絕不會讓聞香老狗擊敗我,絕對不會讓青蓮教就這麼逍遙法外,更不會讓他留下的傷痕就這麼定義我的一切存在。我會戰勝他留給我的痛苦,也會讓青蓮教和它背後的人,無論是寧王府還是誰,都付出代價。」
說瞭我能說的話之後,馬車便再次沉默下來。我眼前的男子似是看著我,也似在看著遙遠的某處。這次唐禹仁並沒有易容,幾個月未見,他原本就棱角分明的臉孔更是削瘦,顴骨高高,讓他的表情顯得冷酷而漠然。那對利劍般的長眉下,冷厲的雙眼若有所思。
良久後,唐禹仁似乎達成瞭什麼結論,原本繃緊的臉龐也柔和瞭下來。他看著我,似乎想要說什麼,又有些難以啟齒。就這樣對視瞭數秒後,他開口瞭。
「謝謝你,阿良……能與你相交,是我之大幸。」
仿佛雨後初霽,陰霾盡散,唐禹仁露出瞭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陽光而溫暖的笑容,充滿瞭感謝與理解之意。
我被這真摯的道謝感染,不由自主地露齒而笑,一股不知該如何形容的暖意在胸腔中擴散開來,讓拂面而過的的秋風感覺格外宜人。
「我的事且說夠瞭,這裡有一件關於你的事,需要跟你提醒一下。」
「哦,怎麼瞭?」
「你的那個朋友,梁清漓……她有點不對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