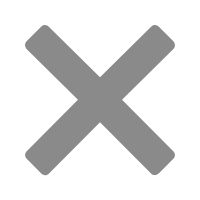第三十八章 絕食祈雨
吏科掌房書吏和戶科掌房書吏神色不善地站著,葉小天翻著賬簿,淡淡地道:“說說吧,僅僅半年功夫,你們兩科的文儀消耗,僅毛筆就有一百八十枝以上。咱們葫縣公務那麼繁忙?還是說這毛筆都是劣次品?”
書吏們都是沒有俸祿和工食銀的,隻靠紙筆費、抄寫費、飯食費養傢糊口,收入微薄。所以但凡做瞭書吏,很難潔身自好,中飽私囊、索賄受賄是常有之事。所以才有這麼一句話:“任你官清似水,難免吏滑如油。”
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再說這兩科的人不是花知縣的人就是王主簿的人,葉小天在這兩科並無心腹,便想揪住此事做做文章,找找他們的別扭。
吏科掌房書吏眼珠一轉,正想找些理由蒙混過去,典慈突然驚叫道:“縣尊大老爺來瞭!”眾人聞聲向外望去,就見花知縣面帶微笑,正站在門口。
花知縣的笑容有些牽強,他是縣太爺,本縣最大的官,要召見一個不入流的小官,人傢竟然推脫不來。這也就罷瞭,他還得紆尊降貴遷就人傢,主動送上門來。
看到眾人驚異的目光,花晴風臉上火辣辣的,急忙暗道:“我的心性修煉得還是不夠啊!要忍!要忍!百忍成佛!”
葉小天看到花知縣,不禁露出一絲意味難明的笑意。他站起身,向吏科和戶科掌房書吏擺瞭擺手,讓他們退到一邊。眾胥吏如蒙大赦,趕緊溜之大吉。眼見這房中氣氛不對,他們這些小魚小蝦可不想沾瞭風尾。
房間裡空瞭,沒有旁人看著,花知縣頓時放松下來,也能真正放下身段瞭。他嘆瞭口氣,誠懇地對葉小天道:“葉典史,本縣悔不該不聽你的忠言啊!”
葉小天隨手提過一把椅子,在花知縣對面坐瞭,訝然道:“大人何出此言?”
花知縣道:“葉典史,你為人機警,善於權變。高李兩寨之爭,由你出面調停最為妥當。可當時徐縣丞主動請纓,本縣想你二人都是初來乍到,既然有意為本縣分憂,那就讓他去吧,畢竟他是你的頂頭上司,不好拂卻他的顏面。誰料那些化外之民無視王法、藐視朝廷,居然把徐縣丞給扣為人質瞭。現在……葉典史,隻有請你出馬啦。”
葉小天恍然道:“啊!原來大人說的是這件事。不瞞大人,卑職當日確曾主動請纓,可那天卑職剛到葫縣,正是縣尊大人為下官設接風宴的時候,下官還不瞭解縣衙情形啊。”
葉小天嘆瞭口氣,對花知縣道:“下官正式署理公務後才知道,徐縣丞已經發下話來,唯有文儀之物交由下官管理,其他一應事務,下官都插不得手。大人,這不在其位,怎能……”
葉小天還沒說完,花晴風便哈哈一笑,擺手道:“葉典史,你誤會瞭,誤會瞭。”
葉小天笑瞇瞇地道:“哦?不知下官誤會瞭什麼?還請縣尊大人示下。”
花知縣一本正經道:“徐縣丞的確說過這樣的話,而且請示過本縣。當時你還沒有上任,徐縣丞擔心奸猾之徒趁機徇私枉法,故而下令,一應案件全要稟報於他,他不點頭不得受理。你正式署理公務時,他去瞭山裡,來不及撤銷這個命令,致有這番誤會。本官這就傳令下去,葉典史既已到任,理應由你負責的事情,就該由你擔當起責任嘛。”
葉小天欣欣然道:“大人明見!”
花晴風立即跟上一句:“如今高李兩寨械鬥,李傢寨更是扣押瞭朝廷命官為人質,此等行為簡直是無法無天之至。葉典史負責本縣司法刑獄,此事責無旁貸啊。”
葉小天馬上愁眉苦臉地道:“大人,下官我有心無力啊。”
花晴風拂然不悅:“有人罔視國法,囚禁命官,你身為本縣典史,對此怎能一再推脫……”
葉小天道:“大人,非是下官推脫,實是無能為力啊。下官要辦案,總要有人可用吧?大人可知下官這典史房中的掌房書吏、快班捕頭是何等樣人?這都是徐縣丞動的手腳。”
花晴風的臉又熱瞭起來,卻還得硬著頭皮應和道:“嗯……徐縣丞此舉確是有欠妥當。這個……如果本縣把人全調整回來的話……”
葉小天把眉梢一揚,振聲道:“那下官就立刻率人入山!”
山野叢林中,八千生苗正向葫縣方向行進著。足足八千人,仿佛成千上萬隻靈猿,步姿矯健地穿行於林間,居然沒有發出半點嘈雜之聲。
哚妮和華雲飛並肩走在一起,雙眼發亮地問道:“你說當時尊者大人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就一把攬過那位瑩瑩姑娘,狠狠地親瞭她的嘴兒?”
華雲飛無奈地道:“哚妮,這一段兒你都聽過五遍瞭,還要問我?”
哚妮兩眼閃閃發光,臉上帶著興奮的紅暈,微微歪著頭,有些迷離神往的模樣道:“我隻是想像不出尊者大人會那麼霸道嘛,他那麼清秀的一個人,嘻嘻,真是太男人瞭!”
華雲飛奇怪地看瞭她一眼,突然問道:“你是不是喜歡我大哥?”
哚妮的俏臉騰地一下紅瞭,急忙否認道:“哪有?你……你不要胡說八道啊。”
華雲飛忍俊不禁地道:“沒有就沒有唄,何必一副做賊心虛的模樣?放心,我這人嘴嚴,不會往外說的。”
與此同時,葉小天也正帶著人匆匆趕向李傢寨。剛剛從收發房調回快班的周班頭緊隨在葉小天身邊,一邊趕路,一邊問道:“大人此去李傢寨,心中可已有瞭定計?”
葉小天道:“這時我能有什麼好辦法?不過正好有這麼一個好機會,我豈能不善加利用?先把你們弄回來,就算這件事辦不成,他一縣之尊難道還能把剛剛頒佈的命令再收回去?”
周班頭一聽,不禁擔心道:“大人,那些化外之民可不敬畏王法,就算縣太爺親自來瞭,他們也未必敬畏。大人千萬小心為上,對付齊木那等人的手段在這些人面前根本行不通。”
葉小天微微一笑:“你放心,我在貴陽時早就見識過他們這等人是如何的無法無天瞭,這種人都是屬順毛驢的性子,我會見機行事的!”
葉小天一行人在山腳下站住,見高傢寨的人把李傢寨圍得水泄不通,大有不死不休之勢,不由微微皺起瞭眉頭。這時候,馬輝和許浩然扶著胖得跟頭海狗似的大亨走過來。大亨接過周班頭遞來的白旗,山上的人很多是羅高李車馬行的夥計,把葉小天一行領上瞭山。
葉小天憑借跟高涯的關系,承諾會妥善解決此事,說動瞭高寨主撤兵。
一團亂麻,總得先找到那個線頭兒,一點點的解開。這種事情急不得,如果亂抽一通,這團麻隻會越來越緊。先勸這老頭子撤回高傢寨,緩和瞭當下局勢,便是一個好的開始。
不管如何,總得先把徐伯夷那頭眼高手低的豬弄回去啊,要不然花知縣那邊又不好交待。隻是……葉小天心思一轉,暗道:“我就白給那個混蛋揩屁股?人,我要帶回去,可一定得讓他吃點苦頭才成。要不然,那個混蛋是不會長記性的!”
一座青色雨簷的高腳樓,樓下隻有五根立柱,兩米多高。有一個人正倒吊在樓下,一身白色的小衣,披頭散發,長發直垂到地面上,正是那位前來調停的葫縣新任縣丞徐伯夷。
徐伯夷因為倒吊著,所以臉龐通紅,額頭卻不知何故一片烏青。
徐伯夷痛得眼淚都流出來瞭,淚水迷離中,隱隱約約看見一個人走到近旁。
那人蹲下瞭身子,歪著頭看他,徐伯夷眨瞭眨眼睛,那張面孔慢慢地清晰起來。葉小天驚訝地道:“哎呀,真的是你啊徐縣丞!失敬、失敬!”
徐伯夷看清來人,不由驚喜道:“是你!官兵上山瞭?哈哈,羅巡檢出動瞭官兵是不是?快!你快放我下來,快把這些凌辱本官的暴民統統抓起來……”
跟在葉小天身後的幾個李傢寨壯漢抱臂站著,聽見徐伯夷這番話,臉色開始有些不善瞭。葉小天嘆瞭口氣:“徐大人,你的腦袋莫非跟我的腳趾頭一樣,用來走路的麼?”
徐伯夷一呆,愣愣地問道:“怎麼?”
葉小天道:“這個寨子有三千多人,調羅巡檢的兵上山?你怎麼想得出來!”
徐伯夷期期艾艾地道:“沒有官兵上山?那……那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葉小天嘆瞭口氣道:“還不是因為你被抓瞭。做調停人做到你這個份兒上,徐大人你也算是前無古人瞭。”葉小天搖著頭站起來。
徐伯夷叫道:“你先放我下來!你去哪裡?”
葉小天道:“這兒我說瞭可不算,徐大人稍安勿躁,待我見過李寨主再說。”
李寨主在樓上盤膝端坐,好奇地打量著葉小天。他已經得到消息,就在剛才高傢寨已經退兵瞭,想來能說服高傢寨退兵的就是此人,倒是不可小覷瞭他。
關於供水問題,其實葉小天一時也拿不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好辦法,對此他避而不談,隻談釋放徐縣丞的問題。這樣一來,至少雙方不會產生直接的沖突。
葉小天曉以利害,李寨主和族中幾位長老不免有些意動。當時是被徐伯夷的態度給氣得失去瞭理智,此時不免有些悔意,他們終究不願與朝廷為敵。但就這麼放徐伯夷離開,他們又有些不甘心。
葉小天笑容可掬地說道:“其實徐縣丞也是一番好意,隻是方法錯瞭,致有這番誤會,徐縣丞懊悔得很呢。方才在樓下,徐縣丞對我說,回去後他要在縣衙前築起高臺,絕食祈雨,以示誠意!一日不下雨,他便絕食一天。令公子可以與我同去縣衙,為他做個見證!”
徐伯夷被人提著腿從鉤子上放瞭下來,直挺挺地站在地上,先讓發脹的腦袋適應瞭一下,這才看到站在面前一臉笑模樣的人正是葉小天。
葉小天道:“徐大人,李寨主寬宏大量,已經不計較你的冒犯瞭,咱們這就可以下山瞭。”
徐伯夷大喜過望,雖然他恨李寨主入骨,可是在人屋簷下,不能不做做姿態,隻得拱起手來,假惺惺地道:“李寨主,過往一切,盡都過去瞭。你放心,徐某是不會放在心上的。”
李寨主傲然道:“你就是放在心上,老夫也不怕!姓徐的,你有個好部下呀,如果不是他再三解勸,老夫又聽說你已許諾,要在縣衙門前築壇祈天,絕食求雨,也算是有幾分誠意,老夫是絕不會這麼容易放你離開的。”
“絕食祈雨?”徐伯夷暗自吃瞭一驚,急忙轉臉看向葉小天。
葉小天一臉黠笑地向他眨瞭眨眼,徐伯夷登時心中大恨:“這個混蛋又要搞什麼鬼?”
李寨主見他對自己的話置之不理,臉色頓時沉瞭下來,不悅道:“姓徐的,你這是什麼意思?莫非這隻是你為瞭下山,有意誑騙老夫的話?”
徐伯夷趕緊說道:“老寨主,你誤會瞭。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豈有出爾反爾的道理?更何況徐某還是葫縣縣丞,當朝命官,許諾過的事更絕不會毀諾背信。”
李寨主聽瞭,臉色稍霽,對葉小天說道:“葉典史,今日看你的面子,我把人還給你瞭。可這旱情未解,河水仍斷,你們如果不能盡快拿出辦法來,李某人也絕不答應。”
葉小天連忙又向李寨主保證一番,這才帶著徐伯夷等人下山。
徐伯夷把他的頭發胡亂紮起,折瞭一截木棍簪好,這才惡狠狠地對葉小天道:“姓葉的,絕食祈雨是怎麼回事,你是不是故意整我?”
葉小天一臉委屈:“徐大人,你這麼說話可就太沒有良心瞭。你可知下官使盡渾身解數,好說歹說,這才說得李寨主回心轉意。下官還替你說好話,說你是心憂災情,情切之下舉止才有些失措,並非有意偏袒高傢,更對李傢沒有絲毫敵意。此番歸去,你將設壇祈雨,以示誠意,這才說得李寨主點頭,要不然你現在還在高腳樓下吊著呢。”
葉小天回頭道:“李少寨主,周班頭,你們兩個當時都在場,你們說是不是這麼回事兒?”
周班頭大聲應道:“不錯,縣丞大人切莫誤會,葉典史所言半點不假!”
李伯皓也微微頷首,哂然道:“若非如此,你以為你能安然離開?”
徐伯夷冷哼一聲扭過頭去,忽然有種不對勁兒的感覺,向葉小天身後的那些捕快們仔細一看,不由詫然道:“他們這些人……葉小天,我葫縣無人瞭麼?你怎麼連倉大使都帶來瞭?”
葉小天笑吟吟地道:“哦,下官剛把大人你救出來,有些事還未及稟報。好教大人知道,知縣大老爺覺得縣丞大人你調整三班六房的舉措不甚穩妥,已經把所有人都調整回來瞭。”
徐伯夷腦袋裡“轟”地一下,看著葉小天那張可惡的笑臉,他的心就像被人丟進瞭一口沸騰的油鍋,煎得外焦裡嫩,那叫一個難受。
他下達的命令,僅僅數日功夫,就被人全盤否定瞭。不要說他是葉小天的頂頭上司,就算他是葉小天的直接下屬,他對職權范圍內的事務做瞭一番調整,命令已經下達,旋即就被上司全部否決,他的臉也要被打成豬頭瞭。
此刻,他應該已成瞭葫縣官場上最大的笑柄瞭吧?他還樹個屁的威信!
下命令的人當然是花知縣,可他清楚,真正促成此事的一定是葉小天,而且很可能就是以他被李傢寨扣住這件事做籌碼,逼得花晴風做出的決定。
“花晴風,真是狗肉上不瞭臺面,爛泥糊不上墻!我怎麼會選擇這麼一個扶不起的阿鬥?早知如此,我該選擇王主簿作為盟友才是啊!”
徐伯夷懊悔他錯信瞭花晴風,懊悔他一時不慎,給葉小天提供瞭反撲的機會,卻絕不會反思他當初之所以選擇瞭花晴風,正是因為他看中瞭花晴風的無能。他相信以他的手段足以鉗制葉小天,他想借花晴風的“名”,出他的“師”,幹掉葉小天後,再順勢控制花晴風。
如今聰明反被聰明誤,他該如何是好?彷徨中的徐伯夷忽然覺得這種感覺異常熟悉。是!當初他被葉小天掌摑,他被從葉小天那裡獲悉真相的展凝兒痛毆,淪為葫縣人茶餘飯後的笑資時,就曾有過同樣的感覺。
徐伯夷怒視著葉小天,咬著牙,一字一句道:“葉小天,這件事我跟你沒完!你欠我的,總有一天,我會叫你千百倍的償還!”
葉小天莞爾一笑,揚聲喊道:“大亨啊!葫縣大旱,百姓生計無著啊。徐縣丞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如今決心在縣衙前面築壇祈雨。我看這祭壇,就麻煩你們‘羅高李車馬行’給造一個怎麼樣?”
徐伯夷氣得七竅生煙,卻聽羅大亨壓低嗓門道:“大哥,你有所不知,我們車馬行正賠錢呢,我現在恨不得一個子兒掰成兩半花。蓋祭壇又沒什麼好處,沒好處的事兒誰幹吶?”
葉小天道:“蓋簡單點嘛,找點木頭釘一下,花不瞭幾個錢。這樣吧,你可以在臺子的四面都寫上你們‘羅高李車馬行’的名字,還可以打起旗子來,算是為你們車馬行揚揚名。”
羅大亨眉開眼笑:“你要這麼說……成!這祭臺我包瞭,回去馬上就辦,今天就能搭好!”
八千生苗在一處大峽谷處停下來,大峽谷中有一條大河,河水奔騰。河道不到百步便是一個極大的落差,形成一道道連綿起伏的瀑佈,河水沖擊的咆哮聲激烈回蕩,聲勢駭人。
哚妮蹲在河邊洗瞭把臉,仰起臉來對站立一旁的華雲飛問道:“你不是說葫縣正在大旱麼,這麼多水,你還說旱?”
哚妮這一仰臉兒,白凈凈的臉龐上還帶著水珠兒,被陽光一照,晶瑩剔透,有一種驚艷的美麗。華雲飛卻絲毫沒給這個小美人兒面子,他白瞭哚妮一眼:“如果這裡有水便葫縣全境不旱,那古往今來,人們還修什麼渠,開什麼河,興的什麼水利?”
葉小天一行人回到縣衙,花晴風見他果然把徐縣丞救瞭回來,大喜過望,先是假惺惺地誇勉瞭葉小天幾句,又對徐伯夷好言安撫一番。
突然有個衙役不等通報,便急匆匆跑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大……大大大大……大人,大事不好啦!有數千番人氣勢洶洶地殺奔葫縣而來,城……城守官已然棄門而逃……”
徐伯夷蹭地一下站瞭起來,大驚失色道:“是高傢寨還是李傢寨的人?”
那衙役面如土色:“小人也不曉得,總之有好多人,好多好多人,至少有上萬人……”
花晴風大駭,頓足道:“這個葉小天究竟是怎麼跟他們交涉的,這些蠻夷定然是暴動瞭。快!我們快走!馬上逃往湖廣。來人啊,快來人啊,快去告訴夫人收拾細軟……”
葉小天笑吟吟地道:“那些人不是來攻打縣城的,那是下官雇來蓋房子的民工。”
花晴風和徐伯夷相顧茫然,喃喃自語:“蓋房子的?”
城頭上,花晴風和徐伯夷戰戰兢兢地探出頭去,就見城下黑壓壓一大群人。城門洞開,城守官早就逃走瞭。其實也怪不得那城守官果斷逃跑,這座小城根本就談不上守禦,他平時把守城門,隻是維持一下秩序,收收入城稅什麼的。
城下,哚妮纖腰挺拔,酥胸高聳,盡力展示她最青春嬌美的一面,大聲喝令族人們肅靜、肅立。她知道尊者就在城頭,心慌慌的不敢回頭。因為不敢回頭,便總覺得尊者正在看著她,所以渾身不自在。她想把自己最美麗、最精神的一面展示給尊者,又不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妥當,難免就有些失措。
其實根本不用她號令,那些族人全都規規矩矩的。雖然他們散亂地站著,不像軍伍一般隊列整齊,但是俱都鴉雀無聲。能讓他們如此規矩,自然是因為他們也清楚,他們至高無上的尊者就在城頭,隻是他們之中大多數人甚至不認識尊者的模樣。
葉小天站在城頭手舞足蹈地比劃:“喏!就是那兒,卑職已經選定,就在那片山坡上蓋房子。那裡本是無主之地,可以省下買地的開銷,地方離縣衙又近,下官每日上衙方便……”
花晴風聽他囉哩吧嗦地說瞭半天建設規劃,不耐煩地道:“那你也用不著這麼多人吧?他們都是你從哪兒雇來的,我看他們服色相貌,都很兇悍的樣子,恐怕不是善類。”
葉小天往城下瞅瞭瞅,道:“他們都是山裡的生苗,貌相兇惡瞭些,其實性情淳樸得很。至於人數……下官原也沒想招這麼多,有幾百人就夠瞭,想必是他們得知下官給的價錢公道,所以一股腦兒都來瞭。不過也沒關系,雇一百個人耗時一年和雇一萬個人耗時一個月,其實花的錢都差不多。”
徐伯夷聽說不是山民暴動,心思已定,沉著臉道:“葉典史,如今葫縣大旱,糧價大漲,你一下子雇來這麼多人,豈不令本縣糧食供應更加緊張?況且,這麼多人進城,難免會造成許多混亂,我看你還是把他們打發回去的好。”
葉小天攤手道:“徐縣丞,你說得輕巧,請神容易送神難吶。徐縣丞如果有辦法,就請你幫忙把他們打發回去吧,葉某人可沒有這個本事。”
徐伯夷剛剛在李傢寨吃瞭大虧,如今這批人是深山裡的生苗,比李傢寨的人更加野蠻,他如何敢出面說話。打發這些人滾蛋?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這些人可是來賺錢的啊。
花晴風蹙著眉頭,幹巴巴地道:“葉典史,你這是要蓋多大的宅院啊?這得花不少錢吧?你才剛剛入仕,有那麼多的錢?”
葉小天微現忸怩之態:“不瞞縣尊大人,葉某是窮光蛋一個,錢是沒有的。不過紅楓湖夏傢有啊,嘿嘿,想必縣尊大人也聽說過我和紅楓湖夏傢的關系。”
徐伯夷睨著他,冷冷一笑,哂然道:“吃軟飯吃得如此不知廉恥,確也少見。”
葉小天嘆瞭口氣,道:“我也不想要啊,可人傢哭著喊著要送錢給我。我想瞭想,有人千方百計想去巴結人傢大戶小姐,可惜就是巴結不上,我也就別拿腔作勢瞭,所以隻好笑納。”
徐伯夷聽瞭不覺氣結。
花晴風暗暗冷笑,對葉小天道:“既是你個人的私事,本官也不便管你。隻是這些工匠都是你雇來的,你一定要嚴加約束,如果他們惹出什麼事端來,本縣唯你是問。”
徐伯夷跟著花晴風往回走,一邊走一邊同仇敵愾地罵著葉小天。還沒有走到縣衙門口,他就被迎面趕來的羅大亨給攔住瞭。
“絕食?”
羅大胖子搓著一雙大胖手,興高采烈地向他表功:“是啊!祭臺已經搭好瞭,徐大人你快去絕食吧,鄉親們都已經迫不及待瞭!”
徐伯夷一聽,臉當時就黑瞭。
李伯皓一看這小子說話太不著調兒,趕緊把他拉開,上前說道:“徐縣丞,祈雨臺已經搭好。葫縣大旱,百姓們久盼甘霖,如今聽說徐縣丞您要高臺祭天,絕食祈雨,都深為感動啊,他們如今都到縣衙門前為你助威去瞭。”
高涯叫人抬著也湊過來道:“徐縣丞,眾望所歸,您快請吧。”
高李兩寨的人並不知道高臺祈雨是葉小天的主意,就算他們誤以為這是徐伯夷的承諾,卻也知道徐伯夷不會關心小民的死活,他提出這個主意隻是為瞭能盡快釋放。
高李兩寨的人釋放他本就並非心甘情願,如今有瞭這借口,還能不好好整治他一番嗎?
徐伯夷臉色極其難看地轉向花晴風:“縣尊大人……”
花晴風一把握住瞭他的手,殷殷然道:“衙內公務自有本縣與一眾同僚代勞,伯夷勿慮,你放心去吧。”
徐伯夷是希望他為自己說句話,隻要花晴風說一句“徐縣丞公務繁忙,不宜絕食祈雨。不如本縣延請幾位大德高僧、有道方士前來作法。”他就好順勢下臺瞭。
誰知花晴風卻是每逢大事必縮頭,根本就沒想過如何替他解圍。本著死道友莫死貧道的江湖規則,花晴風摞下一句場面話,便溜之大吉。
徐伯夷被羅大亨、李伯皓、高涯等人簇擁著來到瞭縣衙門前。花晴風正在衙前瞻仰那座祭臺,一見徐伯夷到瞭,趕緊佯裝沒看見他,舉步進瞭縣衙。
徐伯夷恨恨地瞪瞭花晴風的背影一眼,往高臺處一看,就見縣衙對面倚墻搭起一座高臺,全都是以粗大木料搭成。臺子四周還有擋板,擋板上寫著許多大字,臺上還插著各色彩旗,臺前還有一支鑼鼓嗩吶隊在吹吹打打,許多百姓圍在四周興高采烈。
一見這般情形,徐伯夷鼻子都快氣歪瞭。
徐伯夷迷迷糊糊的就被拉上臺,等他在臺上坐下,這才發現頭頂還給他搭瞭一個遮陽棚,面前還有一甕清水,想得挺周到。徐伯夷一扭頭,又發現身後居然還單獨僻出瞭一個小空間,簾子沒拉上,裡邊赫然擺瞭個馬桶。
徐伯夷一看,心中暗恨:“連方便都不讓我下臺,這是想把我活活餓死在臺上嗎?”
花晴風漫步走向後宅,正好看見蘇雅在花叢前站著,似乎在賞花。
他無意間一抬頭,終於明白瞭夫人方才究竟在看什麼。
他看見瞭一座山,那座矮山本沒什麼風景,它就擺在城裡,大傢早已司空見慣。可今天,那山上卻滿坑滿谷的都是人!挖掘的挖掘、平整的平整、拖運大木的,撬壓石頭的,拆廟的……
花晴風先是愕然,隨即才明白這是葉小天雇來的那八千民工。方才在城頭聽葉小天大談規劃時,花晴風不耐煩得很,並未仔細聽,而且站在城頭看,因為角度不同,他也沒想太多。
此時站在這裡,看著這麼多人在山上平整土地,挖掘地基,花晴風突然間回過味兒來:“這座宅院一旦建成,那麼拉風那麼顯眼地杵在那兒,堂而皇之壓在我的住宅上面,這可是天天、時時打我的臉啊!徐伯夷被拉到衙前示眾打臉去瞭,本縣躲到後宅,你還不肯放過麼?”
烈日炎炎,徐伯夷坐在高臺上,感覺像一隻被剝瞭皮掛起來示眾的野狗,心中倍感屈辱。
這裡連著十字大街,正是葫縣最繁華的所在,來來往往的行人很多,每個經過高臺的人都會對臺上的他指指點點,時不時還會點評一下“羅李高車馬行”那另類的廣告語。
高臺四周就像安瞭柵欄,他坐在籠子裡,雖然這籠子是無形的,他卻無法走出去。烈日當空,頭上雖有遮陽棚卻也不好受,那壇清水他已經喝瞭兩碗,結果解瞭渴,饑火也升起來。
徐伯夷走到旁邊的馬桶間,拉上簾子方便瞭一下,重新回到前邊,往蒲團上狠狠地一坐,咬牙切齒地發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筆帳,我早晚跟你連本帶息算清楚!”
葉小天實際上並不像花晴風和徐伯夷所想的那麼逍遙自在,更沒有得意洋洋。氣候依然幹旱,高李兩寨的爭端依舊沒有平息,這些都需要他去解決。
山坡上,生苗勇士們幹得熱火朝天。他們沒有工錢可拿,可這是給尊者蓋宅子,是在積功德,一想到這一點,他們就感到無比榮耀,唯恐自己出的力氣不夠大、流的汗水不夠多。
不管設計房屋和庭院的匠師們做出怎樣的安排,他們都二話不說,馬上全力以赴。僅僅半天功夫,八千生苗就已經把這座山來瞭個徹底大變樣,到底是人多力量大。
蠱神教歷經一千多年攢下瞭豐厚的傢底,葉小天離開神殿時帶足瞭盤纏,大亨從各地緊急購買的糧食已經源源不絕地送上瞭山。這些大山裡的生苗野外生存能力極強,埋鍋造飯,搭建帳篷,自行解決瞭食宿問題。
葉小天蹲在已被夷為平地的土地廟前面,看著眼前那條潺潺流過的小溪,這座山上有個泉眼,這條小溪就是泉眼湧出的水,所以尚未幹涸。
葉小天喚過華雲飛,叮囑他道:“你輕易不要下山,免得被人認出你來。這裡的人全是生苗族人,別人不敢靠近。明天早上,你陪我到山裡走一趟,咱們去看看你說的那條大河。”
縣衙裡,那些胥吏差役們正在下值,陸陸續續走出縣衙大門。
縣丞正在祈雨臺上出醜,他們自然不好像普通百姓一樣站在臺前大剌剌地觀賞徐伯夷的糗態,但是每一個離開的人都會忍不住往臺上偷偷脧一眼,忍俊不禁地低頭疾走。
徐伯夷在臺上當瞭一天的觀賞動物,已經對此完全免疫瞭。他坐在高臺上,這時候一門心思地盼著天黑。他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隻盼天黑下來,好溜回傢去飽餐一頓。
這時,李伯皓帶著兩個人登上瞭高臺,跟在李伯皓背後的那兩人懷裡赫然抱著被子褥子和枕頭。徐伯夷一見,登時兩眼一黑……
葉小天回到傢,伸手去推房門。手指剛剛觸及門環,房門就吱呀一聲打開瞭,一個少婦打扮的俏麗女子從裡邊走出來,葉小天的手指差點兒按在她那飽滿高聳的胸膛上。
葉小天急忙縮手,定睛一看,趕緊施禮道:“啊!原來是趙傢嫂嫂。”
潛清清向他嫣然一笑,福身一禮道:“葉大人回來啦,奴傢今日到城中買些日用之物,特意來看望瑤瑤,冒昧造訪,還祈恕罪。”
葉小天笑道:“哪裡哪裡,嫂夫人光臨,小天歡迎還來不及呢。”
潛清清俏皮地一笑:“拙夫剛剛上任,諸般事務繁忙。倒是我閑來無事,來葫縣的路上與瑤瑤相處得極好,便來探望她瞭。如果葉大人不見怪的話,以後我可是會常常登門的。”
明月當空,祈雨臺上掛著四串紅燈,四周居然有幾個來自高傢寨和李傢寨的人打地鋪,徐伯夷趁夜回傢大快朵頤的想法徹底破產。不過,花晴風總算還有點良心,跑來看他瞭。
徐伯夷坐在馬桶蓋上,一邊鬼鬼祟祟地從廁簾縫隙裡觀察著外面的動靜,一邊打嗝一邊吃著饅頭。吃著吃著忽然悲從中來,眼淚差點兒掉下來:“我是鄉試第三的舉人!葫縣縣丞!朝廷命官!為什麼……落得這步田地?”
次日,葉小天到深山裡考察那條大河,沿著一條條山脊走,直到第三天,他才探測出一條曲曲折折,以山脊相連,可以抵達高李兩寨中間位置的一條山路。
天色將晚的時候,葉小天帶著人回瞭城。因為終於探明瞭道路,葉小天雖然疲累,精神卻非常好。他走到祈雨臺前,見徐伯夷像隻霜打的茄子,正有氣無力地坐在臺上,不由會心一笑,折身便往祈雨臺上走去。
徐伯夷每天晚上都撐個半死,接著一整天又餓個半死,覺也睡不好,此時正有氣無力地打著瞌睡。見葉小天上來,徐伯夷冷哼一聲:“你鬧夠瞭沒有?若真把本官活活餓死,消息傳回朝廷,你當朝廷會相信本官是為瞭祈雨而死?到時候你葉小天難逃幹系!”
葉小天微笑道:“你若狠得心來去死,葉某情願擔上這場幹系。就怕花知縣送飯來時,足下又要躲在茅廁裡面狼吞虎咽瞭,哈哈哈……”
縣衙後宅,花知縣正在喝茶,蘇雅側身坐在羅漢榻上,拿剪刀細心地剪裁著一塊佈料。
雖然是在後宅閑坐,她的坐姿依舊保持著優雅端莊,一雙長腿並攏著,微微側向一邊,腰肢輕扭,翹臀被繡著荷花的襦裙繃出一個渾圓豐滿的弧度。
花知縣有些不自在,因為蘇雅正在做一件嬰兒服,他二人成親已七年有餘,一無所出。
平日裡每每看到別人傢的孩子,蘇雅都眼熱得很,閑來無事便常常一展所長,做些男嬰女嬰穿的衣服。其實為瞭子嗣的事,兩人曾不隻一次偷偷拜訪過各地名醫,延醫問診,藥湯不知喝瞭多少罐,蘇雅的肚子卻始終不見爭氣。
同民間愚昧百姓把生兒育女的責任統統推給女方不同,古時候的讀書人一樣明白孩子是“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道理。兩人延請名醫時,名醫也說過蘇雅身體正常,花知縣縱然想把責任怪罪到娘子頭上也不成。
況且,花晴風本是窮苦書生,全靠開絲綢坊的丈人傢裡資助才得以安心讀書考中進士,對蘇傢他虧欠至深,在妻子面前更沒有足夠的底氣發威瞭。
再者,為瞭此事,他丈人曾經給他買過一個侍女陪寢,言明一旦懷孕,便可扶為妾室。結果花晴天辛苦耕耘一年之久,那個買來的侍婢也不下蛋。這一來花晴風便知道原因大抵是出在自己身上,一見蘇雅又想起瞭孩子,不免有些心虛。
花晴風正要佯作無事地走出去,一個侍婢走進來,向他福禮道:“老爺,葉典史求見,現在二堂相候。”
花晴風一聽葉小天的名字就心驚肉跳,怵然變色道:“這麼晚瞭,他來做什麼?”